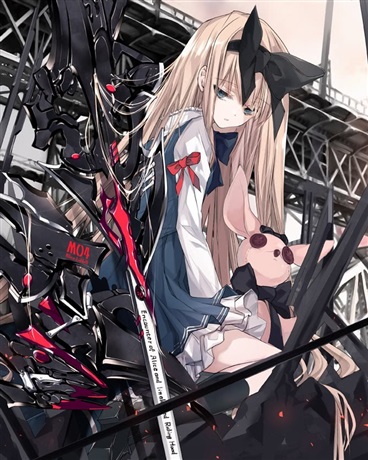被社会遗弃者(一)
“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哈尔茜博士问道。她一动不动地蹲在男孩面前,微笑着,做任何事情来达到他的水平。相反,她仍然站着,她的姿势既不友好也不威胁,只是尽可能保持中立。她的目光稳定而有兴趣。 男孩从房间对面看着她。他只有六岁,但男孩的目光和她的一样坚定,尽管他的眼睛里可能有一丝戒心。哈尔茜博士想,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他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那不仅仅是一个痕迹。他抱着他的身体,就像她抱着自己的身体一样不置可否,尽管她可以从他脖子的紧绷程度看出,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改变,没有任何预兆。 “你先说,”男孩说,然后把他的嘴移到可以笑的地方。 他的声音很平静,好像他已经习惯了掌控局面。那就不怕了。哈尔茜博士想,这并不奇怪。如果她读到的报告是正确的,在他父母去世后的近三个月里,他设法独自生活在矮人星球的外殖民地,一个位于一百公里外的森林保护区中间的非法农场里。在正常情况下生存在一个仍在被改造过程中的严酷世界里已经足够困难了。但是对于一个只有六岁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已经知道你的名字了,”哈尔茜博士承认道。“是索伦。” “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要问?” “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告诉我,”她说。然后她停顿了一下。“我是哈尔茜医生,”她说,笑了。 索伦没有回头笑。她现在在他的目光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丝怀疑,奇怪的是,怀疑就在他的脸上,在他稻草色的头发和淡蓝色的眼睛旁边。“什么样的医生?”他问道。“我是科学家,”哈尔茜博士说。 “不是叹息——,不是叹息——” “不,”她说,笑了。“我不是精神病医生。你见过很多精神病医生,是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 “因为你父母的死亡?" 他犹豫了一下,又点了点头。 哈尔茜博士瞥了一眼小心翼翼地展示在眼镜内部的全息文件。他的母亲显然死于一种特定星球的疾病。治疗是现成的,但是一个远离电网的家庭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男孩的父母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立即向行星官员报告,而是将症状视为感冒而不予理会,继续工作。几天后,母亲去世了,继父生病了。索伦,也许是因为他年轻的免疫系统更容易适应矮人卡,从未生病。根据继父临终的遗愿,他埋葬了双亲的尸体,然后继续住在他们的农舍里,直到补给几乎耗尽,最后徒步出发穿越112公里的蓝灰色森林,到达授权农田的起点。 她考虑让他加入她的斯巴达队是对的吗?他当然聪明足智多谋。他很坚强,显然不会轻易放弃。但与此同时,经历这种经历对一个人会有什么影响呢?没人知道他受到了多大的创伤。没有人确切知道它对他做了什么——可能还在做什么。可能连他都没有。 “你为什么在这里?”他问道。 她看着他,考虑着。没有理由告诉他任何事情;她可以简单地像她和凯斯对其他人做的那样,为他做决定,快速克隆他,绑架他,就像她开始告诉自己的那样,为了更好。但是对于其他孩子,她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他们不会理解。这是一个没有父母的男孩,尽管他只有六岁,却不得不成长得比其他新兵快得多。她能告诉他更多吗? “事实是,”她说,“我是来看你的。” “为什么?”他反驳道。 她回敬了他平和的目光。突然,她做出了决定。“我在努力决定你是否适合我正在做的事情。实验。恐怕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什么。但是如果它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工作,你会比你想象的更强壮、更快、更聪明。” 他第一次看起来有点困惑。“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样的事?你甚至不了解我。” 她伸出手,弄乱索伦的头发,当他没有退缩或回避时,她很高兴。“确切地说,这不适合你,”她说。“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这并不容易;这将是你做过的最难的事情——甚至比你父母的遭遇还要难。” “你决定了什么?”他问道。“我决定让你来决定,”她说。 “如果我说不呢?” 她耸耸肩。“你会待在矮人岛上。行星当局会为你安排一个寄养家庭。”她想,别无选择。他进退两难。她又想知道让男孩做出选择是否不公平。 “好吧,”他说着站了起来。 “好什么?”她说。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后来,回到船上,当她和凯斯交谈时,给他看了她和索伦谈话的视频,他问,“你确定吗?” “我想是的,”她说。 他只是哼了一声。 “就像我肯定要拿走其中任何一个一样,”她说。"至少他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 凯斯说:“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负担。“即使是一个成长迅速的人。” 她点点头。凯斯是对的,她知道。被称为索伦的测试对象的术语不同于其他人——他从一开始就以不同的方式进入这个项目。她必须记住这一点并密切关注他。 任何人 ________ 哈尔茜博士和凯斯中尉都不知道——他们永远也不会发现,因为索伦虽然只有六岁,但却聪明到不会告诉他们——他在这三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索伦,或者他后来称之为索伦-66,不想去想的事情。当他意识到他的母亲已经死了,而她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继父太担心会因为他的非法农场而入狱,所以在她生病时不能带她去看医生。当他继父确信别无选择时,已经太晚了;他妈妈已经走了。 但是他的继父拒绝面对。他把索伦母亲的尸体搬进包厢,锁上门,告诉索伦不可能见到她,她病得太重了,需要一个人康复。持续了几天,直到最后,一天深夜,他的继父喝得太多。索伦偷了钥匙,慢慢地蹑手蹑脚地穿过门,看到她躺在一堆扁平的盒子上,脸紧绷着,蜡黄。她闻起来很难闻。他在森林里看到并闻到了足够多的腐烂动物,知道她已经死了。 他哭了一会儿,然后偷偷溜出房间,关上并锁上身后的门,把钥匙还给继父的床头柜,然后又溜了出去。他坐在厨房沉思,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感觉他的继父对他母亲的死负有责任,就他而言,他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一想到这,他就发抖。 想到这一点以及类似的事情,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最锋利的刀从柜台上拿了下来。他知道这是最尖锐的,因为他妈妈从来没有让他在没有她的帮助下使用它。他必须踮起脚尖才能够着它,它又大又重。他站在那里盯着半灯下刀片上微弱的闪烁,然后慢慢走向继父的卧室。他的继父躺在床上,仍然睡着,微微呻吟着。他有一股酒味。索伦把椅子拉得离床更近,站在上面,现在正逼近他的继父。他就这样呆着,紧握着刀,试图决定如何着手杀死那个人。他知道,他还很小,还是个孩子,他只有一次机会。脖子,他想。他必须快速而深入地戳刀子。也许这就足够了。他会摔倒在继父身上,同时刺进他的脖子,然后在继父做任何事情之前,他会跑进森林,以防它不会杀死他。他突然想到,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是错误的,他的母亲不会同意,但是在文明世界边缘的网格之外长大,生活在一个种植非法作物和对法律不信任的人的统治下,很难知道错误在哪里结束,正确在哪里开始。他很生气。他只知道他妈妈已经死了,是这个人的错。 几年后,当他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他意识到其中有细微的差别,当时他没有机会理解。他的继父有严重的问题,他无法面对妻子的死亡,这让他只是阻止了死亡。是的,一有疾病迹象,他就不把她带到镇上是错误的,但他后来的行为没有那么恶毒,更多的是表明他有多麻烦。但当时,索伦只知道他想让对他母亲的死负责的人付出代价。 他在椅子上泰然自若地等了几个小时,看着继父睡觉,直到光线开始渗入。然后他又等了一会儿,直到他的继父在睡梦中伸了个懒腰,翻了个身,露出了他的脖子。他向前一跃,尽可能用力地把刀放下。当它撞击时,它在他的手里稍微转动了一下,但是它进去了。他的继父发出低沉的惨叫,拍打着他,但索伦已经下床跑出卧室门。他刚打开外门,继父就出现了,他的眼睛红红的,在卧室门口摇摇晃晃,刀从他的脖子和肩膀之间伸出,略高于锁骨,他的衬衫已经沾满了血。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像一头愤怒的公牛,然后索伦把门打开,一头扎进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消失在森林中。他继父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藏在灌木丛里了,刀已经从他的肉里**了,手里还拿着,伤口上喷着生物泡沫。那个人满脸堆笑,显然很痛苦。 “索伦!”他大声喊道。“你怎么了!” 索伦什么也没说,把自己往灌木丛深处拉。他的继父来找他。这名男子声称,如果索伦能站出来向他解释,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走得非常近,非常近,索伦能听到他呼吸的刺耳声音。他的继父差点踩到他的手,然后他继续深入森林,偶尔停下来喊他的名字。 索伦的计划到此为止。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试图杀死继父,就不能再回到房子里去了。然而,他要去哪里?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远离任何东西。 第一个晚上很艰难,黑暗中的空气冷得他一直颤抖着醒来,牙齿打颤。他也不断听到一些事情,不确定是他的继父还是森林中的动物——如果是后者,它们是小啮齿动物还是更大的食肉动物。他妈妈总是警告他不要去森林里太远。“这不像家乡的公园,”她声称。“这不安全。” 他在黎明醒来,又饿又累。他蹑手蹑脚地走到空地的边缘,从灌木丛的安全处看着预制屋,想知道他是否能溜进去拿些食物。他正准备这么做,这时他从窗户里瞥见继父站在里面等着他。他偷偷溜回森林,肚子还在咕咕叫。他想哭,但是眼泪好像没来。他刺伤继父是对的吗?他不确定。无论如何,它没有起作用,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想,他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计划,或者至少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决定,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必须想出下一步该做什么。 第一件事是吃点东西。他不能进屋子拿食物——他应该在刺伤继父之前想到这一点,应该从屋子里拿出一些食物并把它们藏在树林里。但现在已经太迟了。他不得不将就一下。 起初,他试图抓住一只动物,这是一种没有牙齿的松鼠状动物,它像幽灵一样悄悄地绕着树干和树干滑行。但是仅仅几分钟后,他意识到他们对他来说太快了。接下来,他试着一动不动地坐着,看他们是否会来找他。他们很好奇,靠得很近,但离得不够近,他抓不到一只。也许他可以扔石头杀死一个?他试了试,但主要是他的目标偏离了,当他击中一个目标时,它只是发出一声愤怒的叫声,然后逃走了。即使我抓到了一个,他突然意识到,我该怎么做呢?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生火。 那他能吃什么呢?有些植物是可以食用的,但哪些是呢?他不确定。他的家人从未从森林中收获过,而是坚持使用预先包装好的食物。 最后,他踩在一根干枯腐烂的树枝上,听到树枝断裂的声音,一股虫子从缝隙中涌出,很快消失在灌木丛中。他把树枝举起来,看到下面有苍白的幼虫、蠕虫、大颚蜈蚣和有橙色和蓝色斑点的甲虫。他避开甲虫——如果它们颜色那么鲜艳的话,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但同时尝试了幼虫和蠕虫。幼虫有坚果的味道,如果他不太想它们,就可以吃。虫子有点粘,但他可以把它们控制住。几个小时过去了,他没有感到不舒服,他又翻了几个倒下的木头,吃了个饱。 夜幕降临前,他开始实验,离开房子一点点,用不同树木的叶子和针叶做几张床。他发现,有一种叶子,当他触摸它时,会沿着手腕升起一排愤怒、发痒的红色肿块;他在脑海中记下了它的样子,并从此避开了它。他依次尝试了其他每张床,直到找到一张更柔软、更暖和的。他晚上仍然很冷,但不再发抖。他一点也不舒服,但他能忍受,甚至能睡觉。 仅仅几天,他就开始了解他的那片森林。他知道去哪里找蛴螬,什么时候把木头放几天,什么时候把它翻过来。看着鬼松鼠,他学会了避开某些浆果和植物。其他他尝过的。有些很苦,让他觉得恶心,他没有回去。但是有几个他回去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他在灌木丛中看着继父。他早上到那里去看他,当他从房子里出来,到庄稼或把庄稼提炼成白色粉末的加工厂去,晚上也到那里去看他。每次他继父离开房子,他都小心地锁门,尽管索伦几次试图破门而入,但窗户很结实,他没有成功。 “也许我会设个陷阱,”他开始想。他继父可能会介入或陷入的事情,或者可能会落在他身上压垮他的事情。他能做到吗? 他看着。他的继父每天都走同一条路去田里,沿着他自己的脚一天天地刻出来的一条笔直的直线。如果不可预测的话,他什么也不是。这条路很清楚,他不可能不注意到就在上面藏东西或挖洞。也没有足够近的树从上面掉东西。 也许这已经足够了,他试着告诉自己。也许他可以忘记他然后离开。但即使他告诉自己,他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地回来盯着房子。他越来越强壮,他年轻的身体又瘦又硬,没有浪费。他的听觉变得敏锐起来,他的视力如此之好,以至于他现在可以看到在他走过的路上,什么东西在他面前经过的迹象。当他确定没有人在听的时候,他给自己讲故事,低声说寓言,他妈妈告诉他的事情的版本。 几年后,经过深思熟虑,他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既不能进屋,也不能完全离开。仿佛他被拴在上面,就像一只被拴在柱子上的狗。当他长大后,他意识到这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事实上,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索伦每天都变得更加狂野,直到事情突然发生变化。一天早上,他的继父出来了,索伦发现他有问题。他咳嗽得很厉害,弓着背——他病了,索伦恐惧地颤抖了一下意识到,就像索伦的母亲一样。他的继父去收割庄稼,稍微织布,但他无精打采,筋疲力尽,中午时分他已经放弃了,正往回走。只是他没能一路回来。回家的半路上,他跪下,然后平躺在那里,俯卧着,脸埋在土里,一条腿伸向一边。他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索伦认为他一定是死了,但是当他看着继父打了个寒颤,又开始动了起来。但是他没有回家。相反,他爬上卡车,试图爬进去当他失败并跌倒在尘土中时,索伦就在他上面,离他不远,他的脸上毫无表情。 “索伦,”他的继父说,他的声音略高于耳语。 索伦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呆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等待。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他的继父说。“真的。否则我会一直找你。感谢上帝你在这里。” 索伦双臂交叉在他小小的胸膛上。 “我需要你的帮助,”他的继父说。“帮我上车。我病得很重。我需要找到药。” 索伦仍然一言不发,继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一动不动。他一直这样,听着继父的恳求,他越来越恐慌,接着是威胁和哄骗。最后后者进入无意识状态。然后索伦坐下来,呆在那里,为病人守夜,直到两天后他的呼吸停止,他死了。然后他把手伸进继父的口袋,拿了钥匙,收回了房子。 把他的母亲拖出房子埋葬并不是提西的工作,但最终,他的手指因几天缓慢挖掘而起泡出血,他成功了。他的继父埋葬他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他不确定尸体还有什么用处。他喜欢在晚年告诉自己,他埋葬他是为了证明他不像他,证明他更像人类,但他从来不确定这是否是真正的原因。他把他埋在他摔倒的地方,就在卡车旁边,把他卷进一个比尸体还深的洞里,把他周围的泥土堆得很高。 他在房子里呆了几天,吃东西,增强体力。当食物开始变少时,他终于设法摆脱了房子对他的控制,走进森林,慢慢向他认为可能是一个城镇的方向走去。他在森林里呆了几天,也许几周,靠浆果和蛴螬为生。有一次,他甚至用一块小心扔出的石头杀死了一只幽灵松鼠,然后用另一块石头把皮毛切开,吃掉里面松软、苦涩的肉。之后,他坚持吃浆果和蛴螬。 然后,几乎是偶然地,他发现了一条他知道不是动物创造的轨迹,并跟随它。几个小时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小镇的边上,当他从矮树丛中出来时,人们盯着他的眼神让他大吃一惊,他衣衫褴褛,皮肤沾满了污垢和污垢。他们冲向他的方式让他感到惊讶,他们的脸因担心而皱了起来。
光晕进化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救赎TheDreamOfGod
- 三百年前,因为人类的贪婪,神罚降临,世界开始出现名为〔异种〕的吞噬生物,幸存的人类建立名为〔晶壁〕的庇护所,开始逃避这一切。三百年后,随着壁内人对壁外探索的不断进行,来自壁外的少年,满怀希望地看着星空,..
- 23.8万字5年前
- 崩坏3舰长的故事
- 明明我只是来养老的,为什么会遇上这种事啊!"舰长~你在哪啊?来尝尝我做的黑松露牛排啊~"“等等!琪亚娜,你别过来啊!!有话好说,放下你手里的那盘东西!!”(,,#゚Д゚)“啊~”“咕”我下意识吞咽了一下道,“你你,你在里面放了什么?”“诶..
- 59.9万字5年前
- 这里没有神明但是有光
- 这里没有神明,所以没有谁能宽恕人类的罪孽。但偶尔能看见几束光,让这里看上去不太像末日。自从神秘陨石坠落于地球,所有物理原则都像是被神明被篡改了,『魔法时代』开始,但接踵而来的,是来着深渊的罪孽对人类的讨伐……
- 39.5万字5年前
- 无尽终焉2神明战争
- 2479年,御门司命迎来自身注定的命运,曾经的旧识,西尔维娅·吉莲·埃德加德将他带回里世界,开启寻找与对方彼此之间曾经记忆的冒险旅程。只是在重新继承曾经的神明之力后,他突然发现过去的旧恋纷涌而至,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突然发现自己即将面对的不..
- 4.2万字5年前
- 失业英雄的偶像养成计划
- 本书又名《退役反派与失业英雄》世界最恶反派,为何流浪街头?协会最强英雄,为何被迫出道成为偶像?曾经互为宿敌的二人再次相遇,他们的立场却早已改变。神秘的血之契约将两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大叔”和“萝莉”的冒险故事,于此正式展开!(..
- 7.7万字5年前
- 杀戮频率
- 距离末日还剩一个月的时间,重生归来的叶承要如何拯救自己的家人?又如何应对末日之前的好人末日之后的恶魔,该血债血偿还是让坦然对待静待时机?
- 0.8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