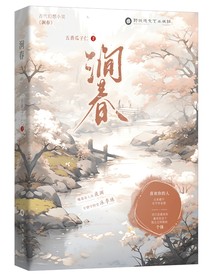毒哑
——世界被毒哑之后,我却觉得吵闹。
——Nachdem die Welt vergiftet und stumm war, fühlte ich mich laut.
(一)
柏林的春,被时代毒哑了。
我坐在窗前,年久失修的窗镜出了裂缝。我不打算去维修它,与之同比的,我希望能借这扇窗,打量一下海因里希曾经的伙伴。
在他身上,我看见了轻柔。
这天下了雪,泠泠的光景,中国人就着那件陈旧的笨重大衣。他们似乎总是很恋旧,旧衣服,旧帽子,剪旧报纸,不时还可以看见他们一些遗留下来的孤本。
他身上添了点雪,我想,他应该去见过海因里希了。他应该已经去过公墓了,日耳曼人年轻的面孔被永恒的贴在墓碑上,仿佛这样就可以获得胜利,获得永恒的生命,仿佛这样就可以逃脱卑贱的命运。
我牵扯着自己,皱着眉努力去回想德国人年轻的面庞。
真糟糕。
我讨厌中国人。
(二)
那个中国人又来了。
这一次他的情绪显得很冷,发尾轻轻垂下来,搭在肩头。我想他应该束发的,拿一条冷色调的丝带,轻轻将发丝系好。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看到这种东亚人的面孔,想法总是很多。这种已经超越了平常人的界限,很奇怪的,我皱着眉盯着他,我确定,我在思考。
助手端来了咖啡,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想,是个好兆头。
我已经不怎么挂念东德了。
死人是没什么好挂念的。
我以人类的惯性来评定,自虐,自负,彻头彻尾的怪物天才。我抬着眼睛,然后轻蔑的扫着他的骨头。
“我想,柏林的冬天应该没有您想象的那样难熬吧。” 他这么说。
我抬起眼睛不动声色瞧了他一眼,然后是冷笑。我规避了中国人假设的一切结局,死亡或挂念,都在一眼间冷却了。
我说:“我以为,你应该被苏联人毒哑了才对。”
不动声色,我看见对面中国人的脸色动了动,然后面部的肌肉在那一瞬间绷紧。很有趣的反应,跟东德一样,会因为一种特殊的人名或者地名,做出奇特的反应。
这样一来便不显得沉闷无趣了。
我听见中国人压低了嗓音,他说:“先生,你很不会看人脸色。”
我从不做那样的事。
我更欣赏这群客人脸色突变的过程。
他是东德的朋友。
我承认了,他们确实很适合做朋友。
只有我在羊亡补牢,在疾疾无名的日子里仓皇回首,然后疯狂逃窜。
——只有我,被留在原地。
上帝赐予我一个世纪的孤独劫难,然后在半路截走,唯一与我算得上是亲近的人。
我是孤独的鬼魂,被毒哑的春天。
Ich bin ein einsamer Geist, ein vergifteter Frühling.
(三)
“没关系。”
这是东德对我讲过的最多的一句话。
他讲德语的时候很沉闷,讲起英文来却莫名的显得温柔又浪漫。
“bady,你还在烦恼什么?”
匆匆夏,他从后背轻轻环抱住我,温热的气息扑洒在耳侧,身上带着冰雪味,冷冽又温和。我说不清那种感觉,但我一闭上眼,便感觉雪白的发丝扫过耳侧。我压根分不清现实,我只分得清东德。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很像的。
长发尾,讲话时的清浅如风,靠近时温柔的鼻息,还有谈及信仰的坚定。
很像。
所以我并不大喜欢中国人。
我分不清现实,但我分得清东德。
我讨厌一切与他相似的事或物,东德只能是东德。即便他死了,我永远记住的也应是东德。
我只爱海因里希。
我愿意记住,属于他的一切癖好。
他是我最恨世界里面最爱的人。
——我并不喜欢这个世界。
战争赋予我的罪名有很多,我无能为力。
我看懂大陆人的眼色,我知道那叫厌恶。我看得懂法兰西,怒到及时,甩向脑门的玻璃杯,碎渣狠狠地扎进皮肤肉里,他们没想叫我活,也没想叫我死。我被夹在中间,兜兜转转,只剩下东德。
我只想有东德。
我只想有海因里希。
我很想海因里希。
从西德到德意志,一直如此。
(四)
没有星光的晚上,眼睛麻木到失去知觉,以他为代表的月亮还是又一次抚平我的伤疤,他的爱好阴险,害得我失去自我,但我还是,心甘情愿。
柏林太冷了,只有依偎才能让我勉强找出属于我的来证明我是一个人类的所属。
亲爱的,下次见面,我要在太阳下。
——Schatz, wenn wir uns das nächste Mal treffen, werde ich in der Sonne sein.
请指认我的心脏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疯子又来啦!
- 修仙小说,随便磕回魂肉魄轮回尽,亦是相回白雪纷。每世抗命残伤奄,血发污衣浸红身。自曾梦影现故因,终是相遇还恩人。二世帮协将死人,长貌如吾一相......
- 2.3万字4个月前
- 涧春
- [已签约]一场让所有人匪夷所思的穿书,沐季珠以为的穿书,其实是夜渊一千两百年来的等待。
- 15.5万字4个月前
- 千秋引岚霜录
- 我的信仰因你而生,所以在我的世界当中,你则是我的神明。————————我不在乎你在别人眼中是谁,我只在乎你是我一人的阿岚,唯一的阿岚
- 0.6万字3个月前
- 荆棘本无意
- 这是荆棘家离开后的故事,莱洛拉受伤被两位老人家救了,却意外害死了这两位老人家。后来,她化名为温溪并认识了阿鹤,结伴与羽逾等人一起去寻找莱洛拉......
- 2.1万字3周前
- 王楚钦:无人知晓的我
- 清冷记者×天才少年“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我想要无人知晓,而你却家喻户晓”
- 2.3万字2周前
- 论千百次回溯
- (写的特烂)白琦和队友一路打灵异,最后却团灭,上天给白琦一次机会,让白琦在回溯中救他们,但白琦一次又一次失败,而这一次的回溯又会有什么不同?......
- 1.1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