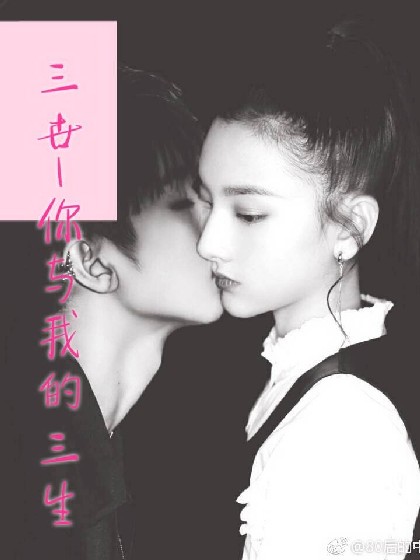第358章珺琪往事六五收吓
第二天我就生病了。
这病来得很突然,很奇怪,也是我二十二年来患病时间最长的一次。
说来也是上苍的恩赐,上苍给了我很多灾难,赐予我很多不幸,可是却给了我一块好身板。从小到大,我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更别说上什么医院。
如今的小孩一感冒便要到医院挂几天吊针,那时的我感冒再重,熬一熬就好了。
这一回,我却差不多病了半个月。
记得那个晚上阿姨走后,我洗漱完躺床上休息,和哥说了晚安之后,就开始做噩梦。噩梦一个接一个。我总是从噩梦中惊醒。醒来时一身都是冷汗。以至于后来我都不敢闭眼睡觉。
就这样,第二天阿姨到房间来喊我起床时,我醒过来,发现自己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阿姨试图扶我起床,我稍稍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不得不重新躺回床上。
阿姨摸了摸我的额头,惊呼不已。
原来我发高烧了。
我本打算和以前一样挺一挺,不吃药也不看医生,可是吃什么吐什么(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食欲),浑身无力这种状态让阿姨放心不下,她熬到下午就再也熬不住,去把街上一个很有名气的女医生叫来了。
一量体温,39.5度,连医生都被吓了一跳。
“我说这女孩子怎么这么能熬,39.5度,再烧下去,脑子都要烧坏。”医生说。
女医生给我吊了三天的盐水,同时一天还打三次屁股针,同时还吃三次药,可是,我的体温却总是降不下来。
药水生效的当儿,体温会在38度以下,可是,一两个小时之后,体温重又升到38.5度以上。
而每个晚上我依然噩梦不断。而每个晚上我都会梦见那已经分成两半的凹凸石壁,梦见那在石壁上闪现的“不离不弃,永结同心”几个字。
有时又会梦见和哥重爬老虎坡,重上擎天石柱,往往在爬到擎天石柱脚底的时候,擎天石柱忽然倒塌,而后吓醒过来。
也会梦见警察突然闯到家里来把父亲带走。我从哭喊中醒来,猛然意识到,父亲已经永永远远地离开了我。
……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阿姨已经挪到平房来陪我睡觉。叔叔阿姨都建议我搬去楼房,但是我不同意,平房里有父亲的气息,我舍不得离开。
阿姨只好到平房来陪我。
有一次半夜醒来,我感觉一片茫然,甚至头脑都有点空白。或许是高烧不退造成的吧?
阿姨给我吃了药后陪我说话。
“琪琪,你几次都在梦里哭喊,哥——哥——喊个不停,我知道肯定不是齐正哲。不会琪琪还有个亲哥哥吧?”阿姨说。
我摇了摇头。
“还有,你总是念念有词,我听又听不清楚,好像说什么离呀气呀,还有什么同心的,你到底梦见什么了?要知道,你不知有多伤心。阿姨的心都跟着碎了。”阿姨接着说。
“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我的意识有点清醒,“醒过来就一点都不记得了。”
“还有,你手上怎么有一个这样的肉瘤?乍一看像是一个肉色的戒指,仔细一看,还有一个小小的凹口,这么多年,阿姨都不曾注意到。是天生就有的吗?”
我点了点头,什么都不想说。
……
女医生在盐水里添加的药换了又换,还是降不了我的体温,她没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行医都三十多年了,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正哲妈妈,你还是送医院吧。”
“要不,”女医生背着药箱离开我的房间,走到房门口她转身和阿姨说话,“你还是找找金莲婶吧。”
“找金莲婶?”阿姨有点诧异。金莲婶是街上一个很会“收吓”的人。
“琪琪估计是吓到了。说起来,我一个做医生的不应该相信这些。可是,很多东西还是信的好。”女医生很是无奈。
“好,那我马上就去找金莲婶。”
待女医生走了,齐正哲拉住他母亲的手,“妈,我看还是让琪琪去住院吧。‘收吓’不是针对小孩子的吗?”
生病期间,齐正哲一有空就来陪我。
“虞医生都这么建议,就先‘收吓’,‘收吓’收不好,再去住院。”阿姨说。
齐正哲没有再坚持。
“收吓”是齐家屯老百姓对一种用土方法应对某种疾病的称呼。一个人被某件突发的事情吓到或遇到、撞到不吉利的东西(这东西往往是阴间里才有的——或可简称为撞邪)生病发烧,而后去请金莲婶一类的人来应对(不同于道士做法却有点像,或可看成其旁支),就叫“收吓”。
不过,这样的病人往往是一两岁两三岁的婴幼儿,绝没有听说像我这么大的成人也还要“收吓”的。
金莲婶很快就被请来了。当然是晚上的时间。我印象中“收吓”总是在晚上进行。不过,后来,当“收吓”成为一种职业之后,也在白天进行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金莲婶。已经六十多岁了,一头银发,慈眉善目。她伸出纤长的手摸了摸我的前额,说了声“好烫”,然后和阿姨交流了几句,便递给阿姨一个用来舀米的竹筒(齐家屯人称之为升筒)。
是一个用旧了的升筒,竹纹都已经被磨光滑了,由此推测找金莲婶“收吓”的人可不在少数。
阿姨拿着升筒出去了。金莲婶在房子里踱步,简单地和我交流了我父亲去世的一些情况。
阿姨回来了,升筒里装了满满的米。
金莲婶接过升筒,把米抹平,而后蒙上一块布,走到我床前,在我平躺的上方对着我晃动升筒,并且嘴里念念有词。
金莲婶半眯着眼睛,一脸的虔诚。
不知为什么,在金莲婶这么操作的时候,我总感觉身体里有一股热流在游走,肚子不停地咕咕叫。我说不清楚那是一股什么样的热流,它走到哪里,哪里便暖暖的。并不是发烧带来的热量,因为那种暖的感觉绝对很清晰。
大约过了半分钟,金莲婶突然往后倒退了一步,发出“啊”的一声,把我和阿姨都吓了一跳。
但我和阿姨都不敢吱声。
就见金莲婶停止晃动手中的升筒,睁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被看得极不自在。奇怪的是,金莲婶停止了晃动,我体内某种东西游走的感觉也即刻消失。
这真邪了。本来极其疲惫的我,又来了点精神。
“琪琪这回可是吓得不轻啊,”金莲婶终于开口说话了。
“是啊是啊,高烧了三四天了。”阿姨说。
“我问一个事,”
“问我吗?”阿姨说。
“不是,我问琪琪。”
“什么事,婆婆?”
“琪琪好好回忆一下,小时候是不是遇上过什么很不同的事?就是,怎么说呢,很怪,很鬼怪的。”金莲婶苍老的声音很有穿透力。
我心里一咯噔。要说我小时候遇到的很鬼怪的事当然是凹凸石的事了,难不成这件事也被金莲婶感应到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可就太神奇了。
“没有。”我这么回答金莲婶。
“没有?不对呀,”这回轮到金莲婶诧异了,“不可能,刚才我做的时候明明感觉……”
金莲婶附在阿姨的耳边说了几句话。阿姨的眼睛瞪大了。
阿姨对我说:“琪琪,你再好好回忆一下,是不是你忘了?”
“真的没有,阿姨。”
“哦,那可能是婆婆感觉错了,”金莲婶说,“不过,我的感觉一向不会错的,今天是有点怪了。这个就先别管了,哲哲妈,我给你看升筒里的米路。”
阿姨凑过去听金莲婶研究米路。所谓米路,指的是刚才被抹平了的米面上在金莲婶一通摇晃之后(严格来说是金莲婶做法之后)显现的凹槽,这凹槽好比一条小路,指向病人受吓的地点。金莲婶结合地形牵强附会(这么说或许是对金莲婶的不尊重)解释一通,指出我受吓的地点就在楼房到平房的拐弯的地方。
金莲婶话一出,阿姨感慨不已,“是是,我说金莲婶,你说得太准了,就是那个晚上我在那里等琪琪回来,琪琪不留意,受了惊吓,第二天就发烧了。”
“哲哲妈,这你就搞错了,我们人吓人哪会把人吓得发高烧的,是那地方有异物,那异物震慑到了人的魂魄,再说琪琪的父亲不是上个月过吗?这里阴气重。”
“对对。”
“那我们走吧,去喊魂。把升筒带上。”
阿姨端着升筒跟着金莲婶往外走,不一会儿便从门外传来她们喊魂的声音。
“路边桥边,河边井边,都回来呀。”这是金莲婶的声音。
“回来喽,回来喽。”这是阿姨附和的声音。
“巷头弄尾,拐弯抹角,都回来呀。”
“回来喽,回来喽。”
……
哥,我之所以跟你详细叙述这件事情,是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那看似小儿科的“收吓”的举动,没有一点科学性的做法,还真把我的体温降下来了。
那个晚上我就没有再连续做恶梦。第二天,虽依旧起不了床,可我已经能吃一点东西了。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虞医生给我用的药恰好在“收吓”那个晚上起作用,这功劳正好被“收吓”占了。
可是谁知道呢?
我只是没有亲自去试验:像金莲婶那样摇晃升筒,会不会随便怎么摇晃,都会有一条米路?
但是,金莲婶做法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体内有一股热流在游走,以及金莲婶总是怀疑我小时候遭遇过什么奇特的东西,这两点还是让我笃信不疑:收吓或许有它一定的科学性。
它还让我联想到:我这病很可能跟擎天石柱裂变有关,因为我做出的决定违背了那八个大字。
可是,等我恢复了身体,能吃能喝能睡之后,再回想这件事,又觉得自己很荒唐——那确实太离谱了。
遇见你是冤还是缘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天才宝宝,买一送一
- 简介:"都说遗传很重要吗?要是我和冷昊轩生下了一个孩子,那我岂不是要生一个天才了?比冷昊轩还好看的天才宝宝!"6年后,她带着成果——腹黑宝贝儿子,重新回到了他的视线里……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15.3万字6年前
- 早安,首长大人
- 简介:“不许和除了我以外的异性接触,懂?”“懂了,大叔。”“要叫老公!”“……老公。”身边带着一个霸道忠犬真的好吗?某女表示非常无奈,也谁叫她这辈子注定是他的女人。某女自从和某霸道忠犬生活在一起后,每天都过着宠宠宠的生活,宠到脚不沾地,爱得深入骨髓。说好的高冷的大人呢?说好的禁欲男神呢?在此之前,他生人勿近,而自从家中多了个可爱小萝莉后,他成了她的专属护花使者,护她一生一世。“大叔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大叔呢?”某忠犬腹黑一笑,“乖乖躺好,让爷宠你一辈子。”
- 17.0万字6年前
- 三世——你与我的三生
- 简介:她满怀真心的嫁给他,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好感,落魄的她无意间怀了他的孩子,却没有料到这个唯一的孩子反而被他最爱的女人害死,最后连她都不放过。就这样,她与他的第一生一世就这样结束了……她与他的第二世,结局还会是这样吗?第三世呢?
- 1.1万字6年前
- 豪门暖婚:老婆大人节操掉了
- 简介:叶简容,温婉大方,恬静美好,识得大体……这些都是假象。她上能爬树,下能摸鱼,还能几天几夜不洗澡橫床上,熏死某男。唐御笙,唐氏执行总裁,商界令人闻风丧胆的鬼才。他冷漠寡言,体恤员工,聪明绝顶……这些也是假象。“老婆,你饿不饿?渴不渴?要不要吃点什么?我最近学了很多点心。”“麻蛋!谁让你们进来的!给老子滚出去!回来!去领一份辞职书。”“老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封杀情敌的。”唐御笙内心独白:没错,他是有意封杀情敌的!本书数字版权由“龙阅读”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04.2万字6年前
- 恶毒女配要翻天
- 简介:一场车祸,十五岁的她高位截瘫,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自那以后,那个豆蔻年华天真烂漫的女孩儿,从天堂堕入了地狱。这一躺就是五年,感觉障碍,失禁,褥疮,肌肉萎缩,它们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她的神经。她不曾屈服,她勇敢善良乐观顽强的生存着,努力着。即使上天真的不公……她以为她的一辈子只能这样了,爱情友情与她相隔千里,她不敢奢求那些,惟愿疼痛能少点,每年生日的那天,她都会许下希望做个正常人的愿望。时间对于何宜来说实在太漫长,为了打发她这漫长的时间,她会在电视上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是功课也不曾落下。闲暇时间也会追追脑残小说,她以为她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却不成想……二十岁生日这天……她居然穿到了一本书里!《霸道总裁的灰姑娘》真是要多老土有多老土的名字,她成了那部文里的终极搅屎棍……角色出场重新开始,顶着胸大无脑心肠歹毒的人设重来一次人生,或许这是上天的眷顾。既然如此,那她一定会好好珍惜!相较于爱别人,她会理智的选择被别人爱。重拾友情,带着闺蜜们走向光明大道。珍惜亲情让她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亲情。爱情?这个小说里最后时刻抓着她的手不肯放开的男人怎么感觉那么腼腆?撩一下下就脸红,靠近一点点就躲几百米远是为什么?看不起她是嘛?不是说好了这个家伙喜欢这个女配喜欢得不得了吗?至于小说里的男主?那时的我你爱理不理,如今的我你高攀不起!
- 0.3万字5年前
- PinkyAdam
- 暂无介绍哦~
- 19.0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