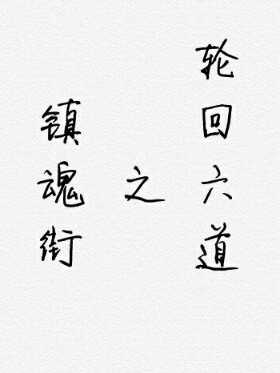五十三章 骑扫把的天使
【卡拉是一只小小狗】
1.
四岁的时候我还不叫杨卡拉,所有人都喊我“杨旭”,听起来像春天里的白色杨絮,一小团一小团飘得漫天。也就是在那个杨絮纷飞的季节里,爸爸离开了家。我对他并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他临走时抱我抱得很用力,小小的我在他怀里疼得哭起来,拍打着他的胸膛说,爸爸是大灰狼。
大灰狼松开我,抹抹眼睛夹着尾巴走了,而我的生活似乎更好了,因为妈妈对邻里街坊说她得道成仙了,看得到凡人的过去未来,窥得见平行世界里的神秘存在。于是小小的院子人来人往,妈妈盘腿坐在一张红木椅子上,说着神秘难解的话,替人趋吉避凶。
我曾好奇地问过她:“你真的是神仙吗?”
她却笑,只给我一个更加神秘难解的答案,她说:“更多时候这是一场心理战和一门语言的艺术。”
可是很多来过的人都说她很神,恭敬地称呼她吴神婆,感激涕零地塞给她很多钱,似乎少了便不能向神明表达自己的诚意。她不接,指指旁边的功德箱,表情恭谨严肃,不沾俗尘,可转天那些钱便会变作我的学费我的新衣或者我的其他。
于是,我总觉得那些衣服上被盖了红红的大印章,触目惊心地写着“功德”两个字,所以即便穿着最新最漂亮的款式我也只是缩在角落里,像终日冬眠的小龟。
吴神婆的名声越传越远,功德箱也满得越来越快。可院子里的邻居却渐渐厌烦起这样的热闹,不满都写在脸上。后来她便用大半积蓄买下了整个院子,一面起居,一面接待来人,一面供奉着乱七八糟的各路神仙。
也就是那年她给我改了名字,杨卡拉。卡拉,卡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反应不过来这是在喊我。
她说这是生辰八字,天格地格,面相手相,经过精心研究才推算出的好名字。不知她有没有算出将来会有一只很有名气的小狗也叫卡拉。
我没有朋友。小一些时,所有小朋友都说我是巫婆的女儿,小心翼翼讨好别人买的零食,却没人敢吃,他们说:你骑上扫把飞一圈我们才理你。于是我跨着扫把从教室二楼的窗口里跳下去。天很蓝,草很绿,我粉红色的小裙子在风里翻飞,可女巫的扫把却没能让我飞起来。
吴神婆在医院里抱着我哭,她说:“我们的卡拉是天使,天使怎么能用扫把飞,天使当然要用美丽的翅膀飞。”
我问她:“那我的翅膀呢?”
她说:“你还小,没有长出来呢。”
我又问:“那你的翅膀呢?”
“妈妈的翅膀被那只大灰狼吃掉了,所以再也不能飞。”她转过头擦眼泪,肩膀在抖,我仿佛看到一对巨大的翅膀在上面扑扇着,随着她抖动的节奏轻轻翕合。于是笃信不已,每天摸着自己的肩胛,查看有没有翅膀生根发芽的迹象。
只是这样的信念在初中便被打破。那时我已经懂了很多,是个忠实的唯物主义乖学生,知道人类对翅膀的幻想已经持续了几千年,更知道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是为何。政治课上老师批判封建迷信的愚蠢,所有人都笑起来,连老师也意味深长地看看我。我便是那个千年不倒的反例,杵在孤零零的一角供人嘲笑。
可是,不论怎样艰难,都要生活都要成长,就像一枚势必抽发的种子,坚强而曲折地在石缝里寻找更多的土壤更多的阳光。
而我也在孤单里,坚强而曲折地让自己宽容让自己快乐。于是我看很多很多的笑话和幽默小说,吃一大包一大包的薯片,原味番茄烧烤麻辣鱿鱼,咔嚓嚓的碎裂声里,孤单委屈冷言冷语通通咀嚼掉。
我还有很多爱好。喜欢一个人站在喧嚣的马路边,贪婪地呼吸摩托车的尾气,那种柴油燃烧未尽的味道莫名美妙。喜欢捡拾地面上的烟蒂,在别人不注意时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一丝熟悉的感觉就飘进鼻孔飘进神经。喜欢自言自语,而言语里却有两个人,一边做絮絮叨叨的自己,一边做用心聆听我的伙伴,有时我会摸摸自己的头发说:“卡拉,不要难过,还有我在呢!”有小小的分裂。
我的偶像是罗永浩,那个以插科打诨闻名的新东方英语老师,一个白白胖胖说话快得没有标点的中年男人。我的MP3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没有一首歌,全是他的《老罗语录》,翻来覆去当作笑话听。
从来,我都是一个人,这些怪喜好也是我全部的闲暇时光。
并不是不渴望友谊,也曾小心而卑微地去取悦他人,想找到一个可以容纳我的群体,或大或小,只要让我安心待在里面,以便看起来不那么怪异又可怜,却一次又一次被隔离在外。
我想,或许友情和爱情一样,需要缘分。那么,也只好静静等待。
2
终于终于,缘分还是不可抗拒地来了,在高中入学的第一天。
照例是新生站在操场上听校领导的长篇大论,然后教师代表新生代表老生代表,各个不知代表着谁的代表轮番发言。九月的天依旧酷热难当,大家在冗长又冠冕的套话里不约而同开小差。我正想着罗胖子的语录暗自傻笑,站在前面的高挑女生就扑通倒在地上。
回头望过去,班主任站在队尾的阴凉里打盹,怪不得他有着考拉的外号,原来与那种嗜睡的小动物有着相同爱好。周围站着的都是女生,丝毫没有要动作的意思。我就走过去背起了她。
她并不很重,可我背着她走出不远,额头上就滴答答开始落汗,右腿的膝盖抖着隐隐地疼。
“喂,校医室在那边哎!”背上的人似乎看出我艰难的脚步,忍不住在我耳边指点,原来我走错了方向。转过头,她在冲我扮着鬼脸,是一只美丽的女鬼。
原来是假装的!我并不迟钝的大脑立即大彻大悟,不过没有揭穿她的意思,两人找了片隐蔽阴凉草地,同流合污起来。
她叫灵子,开朗直率,毫不隐晦地把发言的代表们噼里啪啦数落一通,然后拍拍我的肩说:“还是你够意思啦,不过我好像不轻哦!”
我有些木,张着嘴不知如何接话,长久以来的自言自语让我失去某种能力,好像狼群里长大不懂人类语言的孩子。我只是摇头,笑。
灵子也笑,拉我躺在草地上,随意地问:“你是哪个初中毕业的呢?”
“天源。”我简单地答。
灵子却惊喜起来,“天源?那你一定认识罗浩啦,据说又帅又酷,他做的那个网站很有名气呢!”
我哼哼着不屑:“他啊,除了名字跟罗胖子只差了一个字,还可以接受,其他一无是处!经常逃课,顶撞老师,穿拖鞋上体育课,把女生的情书扔进垃圾桶,吃完饭不刷饭盒……”
我不知为何就开了闸门喋喋不休起来,歪过头却发现灵子一脸花痴相,听得很入神。
我轻轻推她:“你可不要喜欢上他才好,那么糟糕的一个人。”我这样说着难免有莫名的心虚,以至于脸上发烫。
灵子却眨着大眼睛笑嘻嘻不回答,也歪过头来,问我:“卡拉,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呢?”
这样的问题也不假思索就问出口,她那样心无城府,而我却心惊肉跳,张口结舌,像心里最隐暗的角落被人拿了探照灯一遍遍扫过。最后还是咬了咬唇,告诉她:“我妈妈是替人算命的,别人叫她吴神婆。”
灵子愣了几秒,那段空白里我有些后悔,我想我是在亲手葬送这份初现端倪的友谊。可灵子已经把手掌伸到我面前,一脸兴奋地央求:“你妈真酷啊!你也一定懂得不少,帮我也看看相吧。”
我犹豫着拉过她的手,瞄几眼那些细细的掌纹,认真说:“你是金公主命呢!”
灵子一脸诧异:“有这种命吗?好像只听说过金命水命什么的。”
我说:“你是金命的公主啊。好得不能再好了。”
灵子就咯咯笑起来。我也跟着笑,心里狠狠鄙视自己刚才那些讨好的话。
我就像一只仰着脑袋摇尾乞怜的小小狗,等待别人施舍一份友情。
在接下来的班级自我介绍中我被糗住。我站在讲台上微扬着脸小声说:“我叫杨卡拉……”讲台下就笑倒了一片,声声起着哄:卡拉是条狗哎!甚至有男生冲我长长地伸出舌头,我想如果他们有尾巴,也会冲我卖力地摇摆。
灵子忽然就拍了桌子,在所有人的目瞪口呆下站到讲台上,说:“大家知道卡拉·杨吗?”灵子侃侃而谈,把那位举世闻名的音乐指挥家的辉煌成就向全班同学普及了一下,于是我的名字在她口中顿时充满西方艺术色彩。我的外号从“卡拉狗”变作“卡拉扬”。
最后灵子拉着我的手,在一片惊叹中昂首挺胸走下讲台,我露着虎牙偷偷笑,有朋友原来这样的好。
而我和灵子的缘分竟真的强烈到躲也躲不掉,先是成了同桌,后来竟又被调配到同一寝室,睡在对床。
我常常想,上天是否觉察到了以前对我的不公,于是大大地补偿我,在十六岁的那个秋天让灵子晕倒在我眼前,于是我才有了这第一份友谊。我那样庆幸感激,像守护一枚卵一样呵护着它,小心翼翼,诚惶诚恐。
3
只是,那样的年纪里,友谊并不是唯一。而灵子对罗浩的喜欢我从一开始就明了,却不曾想她会那样的执着勇敢。
灵子在球场上拦住他,在许多诧异的目光里说:“罗浩,我喜欢你。”他却不看她一眼,捡起球继续运球,上篮,然后走掉。
灵子说:“卡拉,球衣借我。”第二天她就罩了我压在箱底那件宽大的蓝色球衣站在球场上频频张望,几个男生嘻嘻哈哈逗她,罗浩却没有出现。
灵子又去他的网站,那些帖子都看不懂,全在讨论一些代码程序,却挨个做了回复,通通只是一句话:灵子喜欢罗浩!然后她的ID被封了,那些毫不含蓄的热烈表白也被屏蔽掉。罗浩主动找过来,不耐烦的问她:“同学,你很无聊是吗?”
灵子仰着脸对他笑:“我就是无聊啊,只要谈一场恋爱就会充实不捣乱了。”
罗浩把脸贴下来,一只胳膊抵在墙上,灵子就被逼到墙角,那么近的距离里,呼吸相闻,她看到罗浩的胡茬子黑黑密密,如果吻下来,会不会扎扎的呢?
只是那胡茬子和他热热的呼吸已经越来越远,只留下一句:“还是找别人吧,因为我不像你这么无聊。”
灵子跟我说这些时有些沮丧,但最后还是眼神坚定地告诉我:“卡拉,我不会放弃的。”
那是足足一个学期的死乞白赖,无所不用其极,终于终于,在寒假的第二个星期她得到罗浩肯定的答复。他说:好,就这样吧。
那次她把电话拨到他家里,一个老奶奶接的,灵子甜甜地说:“奶奶,麻烦找下罗浩。”
罗浩刚接过话筒她就大声喊:“我喜欢你——”
罗浩清了清嗓子,然后机智地应对:“你把电视机声音开小一点,说的什么都听不清。”
灵子就咯咯地笑,她知道罗浩奶奶一定没走远,于是趁火打劫:“你答应做我男朋友吧,不然我可要每天电话骚扰你咯!”
那边静了静,然后说:“好,就这样吧。”电话被挂断。
不论如何,她只当罗浩已经答应了她。他是要一言九鼎的!
罗浩竟也真的没有食言,在新学期来到时,开始吃掉灵子买给他的早餐,开始接过她守在球场边上及时递过去的湿巾,有人指着灵子问:是你女朋友吧?他也认真地点头。
那些日子灵子总在五班的门口出没,等罗浩下课等罗浩吃饭等罗浩去打球。我恢复到独来独往的状态,但还是满足的,起码和灵子还是那么亲近,可以分享她与罗浩的那些的甜蜜忧伤,在课堂上的窃窃私语里,在熄了灯的寝室里。
我从窗口里望见他们挨得那么近的肩膀,浅浅微笑,有深深的祝福也有小小的妒忌。
4
时间辗转,已是高二上学期,秋天剩下一只尾巴,还在摇来摆去赖着不走。校园里的梧桐每天都飘落好些大大的叶子,如今只挂一树青荔枝一样的果子。
宁静又凉爽的周日午后,只有我甘于寂寞地留在寝室,趴在床上,嘴里咔嚓咔嚓扼杀着薯片,手上哗啦哗啦翻着一本《青年文摘》,每买到新的一期首先要翻到的自然是笑话那页。
手机响的时候,我正笑得欢,把薯片碎屑喷得满床都是。
屏幕一闪一闪是灵子搞怪的笑脸。她现在该和罗浩在一起吧,怎么会忽然想到我?莫非又是哪科周一该交的作业忘了做,要我帮忙补上?我翻过身按下绿色的接听键,那边惊恐慌张的声音就传过来:“卡拉,快去找罗浩!快点儿,我被绑架了!”
我还未消却的笑就僵在脸上,使了好大力才把卡在嗓子里的薯片咽下去。“灵子,你在哪里,我去救你!”我边嚷边下床,拉开床下的衣柜胡乱翻。
“不要问了,你去找罗浩,让他给我回电话……”似乎电话被抢走,灵子尖叫了一声,那边传来一个男声:“要敢报警,后果你知道的。”冷静沉稳,没有大声吼也没有奸声笑,连威胁也是语气淡淡,点到即止。
“好,我不报警,但你不许……”电话已被挂断。我终于从衣柜底下翻出一把藏银的小匕首,是吴神婆在高一开学送我来时特意放在那里的,说可以辟邪驱鬼。我光着脚丫踩进旅游鞋,朝男生宿舍楼狂奔出去。嘴角还沾着淡黄的薯片碎屑,短发兀自凌乱。
“罗浩——罗浩——”我站在楼下大声喊,喊了几遍四楼的某个窗口才探出一只脑袋,不耐烦地看我一眼又缩回去。他总是这样,好像我欠了他一条命。
于是我仰起脖子,眯着眼睛,声嘶力竭地喊:“灵子被绑架了——”
这下子许多个窗口都探出脑袋来,不友好的声音钻进耳朵。
“这不是高二一班的卡拉扬吗?”
“平时黏着咱们校花,怎么今天又来找校草?”
“别瞎说,听说她老妈鬼魂附体,脑门上有一只鬼眼,小心收拾了你!”
那些窗口像一只只小喇叭,嘈杂的嬉笑被扩大了无数倍,在头顶上不断炸裂开来。
我的心灼热地疼,不为这些习以为常的言语,只是明白多耽误一分钟灵子就多一分危险。我还顾忌些什么呢?迈开脚猛地冲进男生宿舍楼。身后是传达室里大爷的喊声:“哎,同学!女生止步!”
难为大爷这样火眼金睛,我短短的头发,蓝色的校服,和跑得并不优雅的姿势,哪里会像一个女生?!
我刚冲到一楼半就被一条长胳膊拽住:“杨卡拉,灵子呢?”
是罗浩,他正拧着眉毛高高地俯视我,近到无间的距离里熟悉的气息引诱我的思绪胡乱飘飞,可是,这实在不是走神的场合,我跺着脚,呼啦啦喘着气把手机递给他,越是急越是难以成句:“被,被绑架了……要你回她手机……”罗浩真是穷,连手机都买不起,绑匪能从他身上勒索出什么呢?
电话通了,我瞥见罗浩脸色暗淡下来,只对对方说:“我马上过去。”然后几大步就跨下了那些台阶。我跟在他后面像一只笨拙的小狗,气喘吁吁力不从心,恨不得自己蜷作一团一下子滚下去。
我们刚下楼就被追上来的大爷拦住,大爷瞪着我一脸严肃:“哪个班的?跟我去一趟教务处!”
我该怎么办?我想求他,告诉他等我回来即使开除我也无所谓,可是现在,除了去救灵子我哪也不会去。我迈开并不长的腿准备逃掉,手腕却忽然被死死抓住。
还是晚了一步,我逃不掉了!可是我立刻从这样绝望的情绪里挣脱了出来,因为我已经冲出了男生宿舍楼。罗浩正抓着我的手腕大步奔跑,我抬眼望他,可他根本不看我。
我们一直跑到校门口,他才松了手,说:“你回去吧,手机先借我。”
“不行,我要去救灵子!”我这样说着罗浩已经拦住一辆出租车,敏捷地钻进去,毫无商量余地的把我扔在原地。
5
我碎碎地祈祷,念了佛祖保佑又念阿门阿门,信仰混乱,目的单纯。我只想灵子平安无事。可自己的大脑却背叛愿望,抑制不住地联想出很多不好的画面,假象里已经怕得流了一脸泪。
我趴在驾驶座的后面一遍遍央求司机:“拜托您,再跟紧些再跟紧些。”前面的出租车里罗浩似乎在讲电话。
手腕隐隐的疼,举起来看,被罗浩握过的地方留下紫红色的印子。还是迅速放回兜里,用力攥紧那把小小的匕首,后视镜里我的表情决绝得可怖。
我想,为了灵子我可以奋不顾身。
是一处废弃的厂房,周围的旧楼也在拆,残砖碎瓦把本就狭窄的路挤得几乎不见,四处荒凉无人迹。出租车在离厂房还有段距离时已无路可行,不得不停下。
司机大哥问了几遍我来这里做什么都被我搪塞过去,下车前他还不忘好心地叮嘱:“小姑娘,这一带这么荒凉,要注意安全呐!”我来不及说谢也来不及去拿找回的零钱就撒腿跑开,前面那辆出租车已经掉头回来,罗浩却不见了踪影。
旧厂房的门窗都已坏掉,风在里面空荡荡地来回,地面是厚厚的废旧棉花,已经被踩得紧实又肮脏,我的脚步搅动起浓重的霉气。似乎有细微的响动,我慌张地拔出小匕首,四顾着大口喘息,像阴天里极度缺氧的鱼,努力忽扇着腮瓣。忽然听到有人在身后说:“怎么?来的不是罗浩,却是一个小丫头。”
是电话里那个声音,冷静得仿佛没有一丝凶狠残忍。
他戴着一张缀满亮片的紫色狐狸面具,很高,穿黑色的运动装。身后站着一个矮些的人,却更加壮,也遮着面具,是一只绿色的青蛙。一场万圣节一样的绑架。
“灵子呢?快放了她,不然,不然我……”我晃了晃手上的小匕首,手心里全是虚汗。却似乎听到那狐狸面具笑了一声,他远远地望着我,语气依然平静:“回去让罗浩来,这件事你解决不了。”
“你要多少钱,我给!”我急急地喊。
狐狸面具又笑,迈着大大的步子,向厂房后面走去。
我的心突突直跳,一脚一脚,绵软得似乎没有着落。亮闪闪的刀尖慢慢逼近,抖抖的就要触及狐狸面具的后背。刺耳的声音却在此时猝不及防地响起来。
“你报的警?”狐狸面具陡然转过身,眼里的愤怒像两把熊熊的火炬,透过面具烧得我浑身一抖。那只青蛙已经捏紧了我的手腕,匕首落在棉花上,悄无声息。
“我们走。”狐狸面具对青蛙打了个响指示意离开,那只粗暴有力的手才松开。同一只手腕上又多出几道紫色的印痕,火辣辣,像几簇恶毒的小火苗。这一次连骨带肉地疼。
我没有罢休,忽地一下死死抱住了狐狸面具的腰,脸抵在他的背上嚷:“带我去见灵子!不然谁也别想离开!”青蛙的大手又抓过来,像两把钳子夹住了我的肩膀,碎裂一般的痛,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在慢慢松开,坚持得越来越无力。
“带我去见灵子……”我咬牙说着,指甲隔着薄薄的衣服陷进他的腹部。
那个时候我开始后悔,后悔总是那么及时地修理掉我的指甲,不然这样的时刻它该是多么好的武器。
“好了!带上她吧,再不走真要出事了。”狐狸面具终于发话,无奈地掰开我的手。
青蛙咬牙切齿地说了句“多事!”然后在身后重重搡了一把,我就踉跄了一下跟着他们往后面走。厂房后墙没有门,一整片光秃斑驳的墙面上只有角落里开了一扇小气窗,窗口已经架了一只长梯子。
我跟着颤颤爬上去,蹲在小小的窗口里俯视着这三四米的高度,怯怯的。秋日的天空蓝得清澈,地面杂草丛生,这景象好似曾经有过,不知如今给我一只扫把我是否就可以飞得起来?
一只手忽然从身后推了我一把,不耐烦至极地低吼:“快跳!”
于是我的身体就轻了,像来不及张开翅膀的大鸟,向地面急速俯冲下去。风扑面而来,警笛声越来越近。
只是有个黑色的身影在移动,紫色面具上的亮片一闪一闪。他只有0.01秒的时间去思考,可那0.01秒他已经在奔跑。
我软软地落在他身上,只是右腿膝盖露在了外面,与地面接触的一瞬,有种震裂的感觉。还未反应过来疼,已经被拎了起来。青蛙伸手拉起地上的人,问:“没事吧?”
狐狸面具看了我一眼,才说:“没事。”
他们从高过膝盖的草丛里拽出一辆摩托车,白色的机身,白色的座椅。像王子的白马,可惜骑在上面的却是绑匪。
狐狸面具在身后把双手搭在青蛙的肩上,我便被罩在中间,所有感官无处安放,只在车发动的瞬间,猛地吸着鼻子,遗憾那么好闻的味道,却是出现在这样的情境下。
已经黄昏,摩托车驶往更加荒凉的地方,警笛声早已淡去。此去凶吉未卜,或许我已是第二个猎物,却带着义无反顾的决心一路走下去。
他们把我送到一个偏僻的火车站。狐狸面具对青蛙说:“给她买张回市内的票。”我惶惑着要质问,狐狸面具便把手机递过来,说:“你朋友已经安全了,你可以打电话问她。”
白色的摩托绝尘而去。好闻的尾气里两张面具在他们身后飘飞起来,紫色的狐狸和绿色的青蛙。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绑架?我捏着一张回市内的车票,膝盖开始痛起来。表面破了一块皮,白细胞前仆后继而来,封堵着已经快要凝固的出血口。而它的内里恰如久旱的大地,龟裂出清晰可见的缝隙。
微恐悬疑小故事合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奇遇之灵异录
- 简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
- 7.2万字6年前
- 狼人游戏与血夜的复活者
- 威胁着生命的杀戮游戏在一栋巨大的屋子中展开了。这里没有出口,唯有游戏通关才能存活下去。
- 11.9万字5年前
- 七分半的谎言
- 理应死去的同学,突然以‘亡灵’的形式出现在了莫奇的眼前。她的‘死’到底牵扯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 4.0万字5年前
- 光明世界的黑暗
- 让我们跟着黑白无常一起去看一看,那些最可怕的事情吧……(本书不传输任何价值观)
- 0.4万字5年前
- 这个天文社里只有咸鱼而已
- 我不喜欢运动,脑子也不太好使。我不是富二代,但莫名其妙的不缺钱。我很平凡,但我也很忙。我不抽烟,至今仍是单身。所以进入这个三流天文社里的咸鱼只有我而已。本书内容纯属虚构,每周随缘更新。
- 10.2万字5年前
- 镇魂街之轮回六道
- 简介:一个不同的镇魂街
- 1.6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