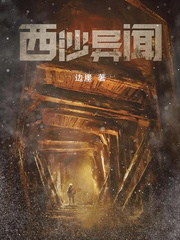三十七章 地行客
一
早上五点多,天色还很昏暗,整个城市被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微光中。卖早点的中年女人拖着三轮车从路边走过,没去注意路面的另一侧立着一个“管道检修”的告示牌。
车轮的声音慢慢远去,突然从那个检修用的黑乎乎的洞口中钻出一个人来,是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头上戴着矿灯,脸上灰扑扑的,还沾着些泥巴。接着另一个男孩子也爬了出来,两人站在洞口对视一眼,嘻嘻笑起来,笑容里藏着一种“瞒住众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的喜悦,然后他们互相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沿着路边慢悠悠离开。
这时天已经亮了很多,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薄雾洒下来,正好落在那两个并肩行走的年轻人身上,暖洋洋的同时,还带有一点儿神秘感。
二
下午我走进教室,一眼就看到廖青阳趴在前排的桌子上,见我进来就对我挤挤眼睛,我忍不住咧开嘴角。
走过他身边时,我停了一下脚步,听到他小声问:“今天去吗?”
“嗯。”我低低地哼了一声,不动声色地走向自己的位子。
至于刚才提到要去的地方,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放学后,我和廖青阳一起去食堂随便吃了点儿东西,正好遇到班上的高维希。
“唐唐,打球去吗?今天约了三班,铁定把他们打趴下!”
我摇摇头,对他说:“才吃完饭打什么球,今天没兴趣。”
高维希眨眨眼,突然凑过来,压低声音问我道:“你们该不会还要去那里吧?偶尔去一次还行,天天去说不定会出事的。”
没等他说完,我马上打断他道:“说什么哪!我和大阳今天要去补课,快迟到了,不跟你废话,先走了啊。”话音未落,我就拉着廖青阳匆匆离开了。
走了一会儿,一直没开口的廖青阳突然对我说:“易子,下次出去外面吃吧,拒绝多了会让人怀疑。”
我摆摆手道:“你别那么紧张,只有高维希知道嘛!再说了,一开始也是他带我们去的,用不着瞒他。”
廖青阳低下头嘟哝道:“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我一下子笑起来,扬手一巴掌拍在他的背上,“哈哈,对,这是秘密!”
其实所谓的“秘密”并不是没有其他人知道,只是因为它特殊的神秘感,我们乐于把它当做“秘密”,那里就像是隐藏在现实世界阳光下的影子,存在着,却一直被忽视着。
说着话,我和廖青阳绕过学校的田径场,进入配电室旁边的一间废弃仓库,顺着竖梯爬下去,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杂物,光线透不下来,几乎寸步难行。
廖青阳拧开手电走在前面,我紧跟着他,又走了一会儿,旁边的砖墙逐渐变成了嶙峋的石壁和土层,空气里弥漫着阴冷腐朽的味道,吸进肺里,却让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尽管已经来过好几次,但每一次进入地底的感觉还是让我有些激动,还有一点儿紧张。
这时已经真正到了地下,周围很安静,我们都下意识地放缓了呼吸,拐过一个狭长的土洞,毫不意外地看着散落在地面和土墙中的骨头,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人骨。我们学校背后曾经是一块坟地,现在规划出来盖了楼房,地面上已经找不到那些被推平的土坟,但是地下却真实地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我们把这个区域称为“地下墓穴”。
那些发黑发黄的骨头大多是破碎的,好几个死者一起裹夹在土块中,已经分不出彼此。要从这里过去,一定会踩到碎骨,我已经尽量避开,还是听到脚下发出噼啪噼啪的碎裂声。廖青阳伸过手来拉住我,他走得很稳,并且毫不迟疑。
穿过“地下墓穴”,又走了十多分钟,洞穴不再是单一的道路,开始变得四通八达、纵横交错,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心区域。
这里比刚才嘈杂很多,非常容易迷路,好几个洞口闪着不同颜色的灯光,各色各样的人藏在各自的洞穴里,偶尔可以听到有人大声唱歌,还有架子鼓发出一连串吵闹的鼓点。
我的头有点儿晕了,幸好廖青阳记得路,带着我东拐西拐,终于进入一个宽敞的地下洞穴。
这个洞空间很大,沿着洞壁插了一圈点燃的蜡烛,所以光线还算好,迎面看去,洞里最大的一面墙壁上画着几簇巨大的海浪。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个人在里面了,看见我们都友好地打招呼,廖青阳径直走向画着海浪的那面墙,找出堆在角落的颜料,我也过去帮忙,把颜料一一摆开。
“今天要画什么?”廖青阳问我。
我想了想道:“随便,说不定会画一片森林。你呢?”
“还不是一样。”
说着,他用笔蘸了黑色的颜料在墙上勾出一个圆形的轮廓,然后细心地涂满。
前几次我问他那是什么,他告诉我是黑色的太阳。每次来,他总喜欢先画一个黑色的太阳,接着在太阳下面画出人,人物画得很简单,净是些日常生活中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动作。这些动作我在地面上看过无数次,但是在这里看又有不同的感觉。
说到这里,我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地方了。这里属于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只不过它藏在地下,就像城市的倒影。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它的存在,这些人更愿意称它为“地下世界”。
据说这个“地下世界”是从巴黎得到的灵感。传说整座巴黎城下密布着四通八达的管道、地铁、墓穴和采石场,连成一个庞大的地下城市,我们这边虽然比不上巴黎的规模,也算小有成就。
最开始是由几个人挖通地下隧道,连成一小片区域,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把通道拓宽,开凿出更多的洞穴。来这里的人形形**,有落魄的作家、疯狂的艺术家、冒险者和不法分子,他们在见不到阳光的地下演出、开派对、创作、吸毒……
这里的人们享受着无政府状态下的绝对自由,抛弃地面上的束缚,解放自己,做想做的事,哪怕只是蜷在黑暗的角落抽上一根烟。
我们中间最先知道“地下世界”的人是高维希,尽管我并不清楚他从哪里获得的信息,这个人平时就喜欢猎奇,半个月前他兴致勃勃地拉着我和廖青阳进入地下。第一次来的就是这个画着海浪的洞穴,里面的人叫它“海滩”。这里聚集的大多数是年轻人,有其他学校的,也有已经辍学的,大家年纪相仿,相处起来很容易。
后来我和廖青阳发现学校的废弃仓库竟然可以通到这边,于是来得更频繁了。我们在地下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涂鸦,廖青阳画他的黑太阳,我画的都是植物,比起人类,我更喜欢这些沉默的生命。
我很享受这里的氛围,可以不受打扰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画画是我从小的爱好,但是考虑到实际因素,当初几乎没有犹豫地放弃了考艺术生,老老实实埋头在一大堆书里。
直到我在地下重新拿起画笔,才明白我对它的喜爱有多深,这让我更加舍不得离开这个昏暗的洞穴。
“地下世界”的人喜欢称自己为“地行客”,我觉得这个称呼很酷,现在我也是其中一员了,至于廖青阳,我看得出来他也很喜欢地下的环境,甚至比我更喜欢。
倒是拉我们进来的高维希,来过几次以后就兴致缺缺,加上高考日益临近,他就来得少了,最近一次也没来过。
好在高维希没有再向其他任何人说起“地下世界”的事,我和廖青阳严守着这个秘密,就像守住我们的精神家园那样慎重。
那种郑重其事的心态说起来荒唐,好比心里藏着一个“秘密”,短时间内会让人感到无比骄傲和刺激,仿佛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了。这个道理在年轻人身上最能够体现出来,我也是到很久以后才明白的。
三
第一次模拟考的成绩公布,伴随着两个坏消息。
一是廖青阳考砸了。他的成绩一向很好,但是这次考试下滑了一大截,这样直接导致原本最有希望获得保送资格的他失去了机会,保送名额落到我们班另一个同学头上。当然,理由是班主任说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同学当教育局长的老爸在其中起到了多大作用。
另一个坏消息是,“地下世界”的两个洞穴陆续发生了坍塌,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很多“地行客”担心还会继续出事,因为这些洞穴在开凿时没有做任何加固措施。反应最大的是“海滩”,那些年轻人来这里纯粹是为了玩乐,谁都不想为此搭上一条命。
坍塌事故发生以后,我和廖青阳下去过一次,“海滩”里几乎没剩下什么人了,本来就宽阔的洞穴愈发显得空荡荡。廖青阳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心里的失望,我也觉得很不是滋味,本来在这里的那些日子是最愉快的时光,现在我们却好像被众人抛弃一样。
模考之后学业一下子紧张起来,每天忙得昏天暗地,我几乎抽不出时间再去“地下世界”了,想想“海滩”的冷清景象,也没什么兴致。
过了一个多星期,班主任突然找我去,对我说:“唐易,我知道廖青阳没拿到保送名额一定很沮丧,他这段时间请假很频繁,经常不来学校,你和他是好朋友,平时多安慰一下他。凭他的能力,我相信可以考上好的大学。”
我有些吃惊,这段时间太忙了,竟然没有发现廖青阳请假那么多天,之前以为他只是普通的生病,现在想想,他的身体一向很好,不太可能生什么大病。
保送的事情我也没有好好和他沟通过,只是安慰了几句,他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倒把我蒙住了。
廖青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放学后,我丢开堆积如山的习题,去了那间废弃仓库。
不出我所料,廖青阳果然在“海滩”,我进去的时候他没有画画,而是缩在角落里睡觉。
因为猜到他很有可能在这里,我一开始就没有去他家里问,廖青阳的父母很严格,家里的人对他寄予了相当高的期望,如果被他们知道廖青阳成绩下降,而且几天不去上学,免不了又是一通责骂。
洞里的蜡烛燃了大半,摇曳的光影在廖青阳的脸上跳动,他看上去很疲惫,眼睛下面挂着浓浓的黑眼圈。我没有叫醒他,而是默默地在旁边坐下。
无聊之中我就去看墙上的那些涂鸦,我的森林基本完成了,郁郁葱葱一大片,廖青阳的黑太阳就挨在森林旁边,大大小小的黑色圆形分布在墙面上,使太阳下面的那些小人变得古怪,尽管每个动作都很熟悉,但是那些姿势非常僵硬,在昏暗不明的光线里更加显得诡异。
看着看着,我后背一阵发凉,就听到廖青阳在身后叫我的名字。
我回过头去,问道:“醒了?吃饭没有?”
他指指旁边揉成一团的面包包装袋,我不由皱起眉头。
廖青阳问我:“你怎么来了?”
“来陪你呀,顺便把森林画完。”
听我这么说,廖青阳的精神似乎好了点,把绿色的颜料挑出来放在我身边。
“大阳,保送的事…”
廖青阳摇摇头,表示不在意,然后蹲下来继续他的画。我拍拍他的肩膀,也在旁边画起来。
“易子,你觉不觉得,要是以后都能在这里生活就好了?”
我侧过头看见他黑亮的眼睛里闪着认真的神色,手中的笔忍不住一抖。
“虽然我很喜欢这里,但生活的重心毕竟在地面,你忘了?我们约好考同一所大学的,你在地下怎么高考?”我半开玩笑半劝诫地回答他。
廖青阳突然拔高了声音道:“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然后呢?大学毕业还要找工作,明里暗里的规矩一大堆,你永远被束缚在那些莫名其妙的规则里!但是地下不一样,这里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们藏在这里,没有人找得到!”
“这里也很危险!快塌了你不知道吗?!永远待在这里和自杀有什么区别?想做什么做什么?要是我想晒太阳呢?这里有吗?就靠你的那几个黑太阳?!”我不由自主地和他对吼,吼完以后才发觉刚才说的有些过分了。
廖青阳愣了一会儿,又转回去面对着墙壁,不再跟我说话了,我很想跟他道歉,但是那句“对不起”始终说不出口。
我们之间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尴尬,只能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画笔上,洞穴沉默在一片黑暗里,安静得有点可怕。
这天晚上,我和廖青阳谁也没有离开,画了整整一夜的涂鸦,五点多钟的时候我实在撑不住,靠着墙眯了一会儿,醒来时他已经不见了,墙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小人,都摆出同样古怪僵硬的动作。
那之后廖青阳一直没来上课,我原本计划在学校里向他道歉并和好的想法没法实施,班主任又找过我一次,问我知不知道他的情况,我帮他编了点儿理由,看得出来班主任半信半疑,如果再过几天他还没出现,恐怕就要通知家长了。
四
两天以后,廖青阳突然来上学了,我一进教室看到他坐在里面,惊讶得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好像没看到我似的,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一整天上课我都在踌躇怎么对廖青阳开口,放学的时候他却自己来找我了。
他说要带我去看一个地方,就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往外走,让我产生了一种前几天根本没有吵过架的错觉。我以为还是要去仓库那边,没想到他直接把我拉出学校,坐着公车一路到城郊。
“你到底要去哪里?”
廖青阳停下脚步,看向旁边那条小河,这条河水量不大,城郊这一段是天然形成的,后来被挖到了城里,充当景观河。
廖青阳指着河面上的一座小石桥,对我说:“桥洞下的河道侧面有一条水道,从那里游过去可以进入一个秘密的洞穴。”
我惊讶道:“那个洞是独立的?”
廖青阳摇头说,“也通向其他地方,如果要从地下过去必须穿过‘蜘蛛网’。”
我立刻变了脸色,问他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洞的?”
“听几个‘地行客’说的,我去‘海滩’的时候遇到他们……”廖青阳的表情不太自然,垂着眼睛没有看我。
我当然知道“蜘蛛网”是什么地方,“地下世界”龙蛇混杂,看起来没什么约束,其实不同的人只在自己的圈子里活动。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地下通道进行各种交易,每个“地行客”都是知道的,只是没有人去管别人的事,这些自发形成的小团体之间壁垒分明,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任何形式的交流。而那个“蜘蛛网”,就是指不法分子集中的区域,我们这些人平时都尽量避免靠近。
以前我和廖青阳约好,只做自己的事,绝不和那些人搅在一起。但是现在,他口中那几个“地行客”一定不干净,很有可能他已经瞒着我去过了“蜘蛛网”。
“既然知道跟那些人有关系,还来干什么?”我说话的口气不大好。即使喜欢“地下世界”的自由,是非我一向分得很清楚,不该碰的东西永远不会碰。
廖青阳支吾半天,才小声说道:“据说这个洞里的人从来只在地下生存,我想去问问他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留在地下。”
“你还在想这件事!”我道:“这种事情你也会相信?怎么可能是真的?”
“可是……那些是‘五月花’的人……”
一听到“五月花”这个名字,我愣住了,任何一个“地行客”都听说过“五月花”,这是最初开辟“地下世界”的人的自称。可以说,如果没有“五月花”就没有今天的“地行客”。不过随着“地下世界”越来越复杂,现在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们了,我一直没搞清楚“五月花”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只能猜测他们想效仿那艘从英国开往北美的“五月花”号帆船,成为新世界的开拓者。
既然搬出“五月花”,也难怪廖青阳会相信了,我放软语气对他说:“在地面上不好吗?你的基础那么扎实,现在开始努力肯定考得好,等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廖青阳的眼神很痛苦,慢慢摇头道:“只要是在地面,我就永远得不到自由。”
我叹口气,拉着他回去,边对他说:“总要试一次才知道。这段时间就不要去地下了,我陪着你一起,熬过这几个月,然后我们一起上大学。”
我们又坐上公车回城,廖青阳家和我家不在一个方向,我必须先下。
跳下车的时候,听到廖青阳对我说:“易子,好好考。”
我闻言转身,笑道:“你小子是讽刺我不如你吧?我不会让你得意下去的。”
这时车门已经拉上了,车屁股一抖,慢慢向前开走,我站在下面看着廖青阳,车里很拥挤,甚至看不清他的表情,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已经离我很远。
不久以前我们还肩并肩走在晨曦中,但是现在,那种守着共同的秘密相视一笑的亲密已经不见了,廖青阳的眼神让我感到陌生,有一种逃离“地下世界”的冲动,躲得远远的,回到之前乏味却平静的生活。五
一到家,我就给高维希打了电话,问他知不知道城郊的河中洞穴和“五月花”的关系,高维希说他没有听过,不过可以帮我去问问朋友。
第二天去学校,高维希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怎么知道那里的?”
“廖青阳告诉我的,他说那里是‘五月花’的地盘,洞里的人从来只在地下生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听不出来?在地下生存,还不是因为见不得光!这个‘五月花’神神秘秘,被传得很邪乎,你告诉廖青阳,千万不要靠近。我朋友说,他们做的都是犯罪的事。我猜啊,‘五月花’的人说不定和毒品有关系。”
我心里一凉,之前被廖青阳的思路影响,说是在地下生存,竟然没有想到那是象征的说法。
这么想着,我下意识地把目光转向廖青阳的座位,他仍旧没有现身,我甚至怀疑他昨天根本没有回家。
高维希又说:“最近有好几个‘地行客’失踪,据说是走入地底深处迷失在里面,可能就是他们搞的鬼,你们自己小心点,这几天‘海滩’那边就不要去了。”
我心不在焉地点头,突然想到昨天我和廖青阳说到同样一句话的时候,他到底听进去了几分,是不是也这样心不在焉。
第二天,廖青阳还是没有来,我去“海滩”找过他,但是那里空无一人。
意外的是,过了几天班主任带着两个警察把我从教室里叫了出去。
“你就是唐易?”其中一个警察问。
我点头。
“廖青阳是你的好朋友?”
我又点头,心里的不安在逐渐扩大。
“听你们老师说,他很长时间没来学校了,你们既然是朋友,知道他这几天的动向吗?”
我感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问:“廖青阳出事了吗?”
“他有没有出事,我们不知道,不过你知道‘海滩’吧?就是你们经常去的那个地下洞穴。”
我的脑子里突然嗡地一声,“秘密”被他们知道了!而且还是警察!班主任一定也知道了!还有谁?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你不要紧张。”那个警察安慰说:“只是因为最近好几个年轻人失踪,他们的家人来报案,调查的时候顺便问出来有这么个地方。我们问过很多经常去那里的人,‘海滩’也是他们说的,据说你和廖青阳也经常去,所以来问问情况。”
听他这么说,我稍微放松了一点,也冷静下来,把这几天的事都跟他们说了,包括学校里的秘密入口,不过关于廖青阳和我的一些细节,我并没有告诉他们。
警察好像对“地下世界”特别感兴趣,让我详细描述一下那里的情况,听完以后,两个警察都皱起了眉头。
“谢谢你的合作,廖青阳的行踪我们会继续调查,那个‘地下世界’你以后就不要去了。”
他们离开后,我竟然有一种事情才刚刚开始的感觉。
廖青阳继续失踪,我想再去“海滩”看看,却被在“地下世界”的外围被警察拦住,我发现四周都拉上了警戒线,那些警察还打算盘问我,我找借口溜走了。
第二天,上次的两个警察又找到我,他们问的问题似乎都围着廖青阳打转,而且一个比一个详细,我看他们眉头紧锁的样子,忍不住问:“是不是廖青阳出事了?”
他们对视一眼,其中一个说道:“失踪的那几个年轻人的尸体在‘海滩’的涂鸦墙里被找到,廖青阳可能是嫌疑人。”
我霍地站起,拔腿就想往外冲。
一个警察拦住我道:“你干什么去?”
“我要去‘海滩’看看!”
“那里是案发现场,现在已经封锁了,你进不去!”
我还想向外走,那个警察说:“我们这里有现场照片,你要看吗?”
我盯着他手里的牛皮纸袋,忽然冷静下来,对他道:“看。”
他把照片递给我,同时道:“你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不太好看。”
我一张张地翻着那些照片,心里爬满了鸡皮疙瘩。尸体的模样确实很不好看,已经开始腐烂了,但是让我在意的不是那些,而是他们的动作——全都摆出僵硬古怪的姿势嵌在墙内。
照片拍得很清晰,我甚至能看见尸体旁边没有挖开的墙面上有我画的森林和廖青阳的黑太阳,当然还有他那些诡异的小人,墙后面的尸体和小人异常相似。
我抬头看看两个警察的表情,显然他们也发现了这一点,难怪会认为廖青阳就是凶手。
我默默地把照片还给他们,接着高维希也被叫去问了一遍,他提供了我这几天的行踪记录,消除了我的行凶嫌疑。
几天以后,在这个案子中,廖青阳几乎已经被当成最大嫌疑人,但是没有人找得到他,警方后来又找过我几次,都没有什么收获。
我进不去“地下世界”,也不愿意去廖青阳家里见他的父母,多日来的担心成为现实,廖青阳彻底和我失去了联系。
“地下世界”曝光在众人眼中,政府开始填补这个漏洞,禁止任何人进入地下,数不清的洞穴被施工队运土填起来。“地下世界”在一夜之间成为地面人热议的话题,他们把那里称为“犯罪者的温床”。
“地行客”好像也在突然之间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他们藏在哪里,那些站在阳光下衣着光鲜的人,很可能就是不久前潜行在地下的一员。
高维希似乎很高兴能与这次案件有关联,经常拉着我讨论案情。
说到后来,连他也认为廖青阳是杀人凶手,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搜肠刮肚,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来反驳他们。
“易子,你真的不知道廖青阳在哪里?”
我第八十一次摇头,他还是有些不相信,“你们俩那么好,他走了怎么会不告诉你?如果我是他,肯定信得过你。”
我还是摇头,廖青阳没有和我告别,他什么时候消失也不给我一个信号,我甚至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就被告知了这个事实。想起那几天断断续续见到他的几面,就像做梦一样毫不真切,晕乎乎地想了一圈,只记得他在公车上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易子,好好考。”
这话在脑袋里重新闪现,每个音节都拉得很长,还有那看不清表情的脸,让我烦躁得想掀桌子。
高维希突然说:“廖青阳会不会被‘五月花’的人抓去试药了?”
我猛地打了个激灵,城郊外的洞穴!他会不会去了那里?
我顾不得还是上课期间,急匆匆地向班主任请了病假,因为廖青阳的事,她这几天对我很宽松。
我冲到校门口,想了想又去废弃的仓库找到一把生锈的铲子,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一路开到城郊。
河面上的小石桥还是上次那个样子,不同的是这次廖青阳没有和我一起。望着流速缓慢的水面,我只是稍稍犹豫一会儿,就干脆地脱掉上衣,拿着铲子下了水。
沿着河岸摸到水道的位置,脚边能感觉到水流涌入的方向,深吸一口气,我沉入水中,顺着水流向前游。
原本以为会花很长时间,实际上只是一会儿,水流很快就慢了下来,几乎是静止,意识到可能已经到了,我赶紧浮上去呼吸。
抹掉脸上的水,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洞穴中,比不上“海滩”那么宽阔,但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水漫到洞穴的中间,旁边是一圈石台。
我爬上石台大口地喘气,一阵后怕涌了上来,下水的时候根本没有多想,如果有人在这里面,我恐怕是凶多吉少。
休息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检查这个洞穴,找到两处通道,但是已经被堵住了,看来政府的清洗也波及到这里,那些人已经逃走了。
洞内一眼就可以看到头,没有“五月花”,也没有廖青阳。我非常失望,正准备离开,猛然瞥见一侧的洞壁上画着一个小小的黑太阳!
廖青阳绝对来过这里!
我激动地摸着墙上的图案,不由得想起“海滩”墙壁上的那些小人,一个怪异的想法滑过我的脑子,几乎是同时,我已经站起来,举起铲子就在黑太阳的位置上敲。
这里和“海滩”一样,洞壁刷了一层石灰,很容易就被敲下来,露出里面的土墙。
我知道这个想法很疯狂,手指不由得颤抖,但是握铲的手却停不下来,机械地挖出大块大块红土。
很快,土墙里露出一个人的脸,虽然被土遮了大半,我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是廖青阳的脸。
又挖了一会儿,他的身体也露出来,手放在胸前,显得很安详。
我不知道当时是哪来的勇气,不顾尸体半腐的恶臭,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确认他身体上没有任何外伤,再加上这个姿势,显然廖青阳死前并没有挣扎,我控制不住地想象,他被封进洞壁之前还是活着的,只是沉入了睡眠。
心情复杂地看着他,准确地说是他的尸体,悲伤、痛苦、焦躁、遗憾、失而复得甚至如释重负,说不清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出一句:“大阳,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廖青阳没有回答我,他当然不会回答我。我在他旁边坐了很久,脑子里木然一片。其实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我一直有预感,只是不想承认,如今由不得我不承认。
他是自杀?还是他杀?我偏过头去看他的脸。
“廖青阳会不会被‘五月花’的人抓去试药了?”
高维希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原本最不靠谱的推测偏偏成了唯一的可能,难道廖青阳真的是死于“五月花”之手?
不过我想,即使是“五月花”下手,也是廖青阳自愿的,我隐隐觉得他是自杀,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
直到傍晚,我才起身,离开前又鬼使神差地把他的尸体重新封进洞壁里。既然是廖青阳自己的选择,我能做的只有尊重他,帮他守住这个最后的“秘密”。
回去的路上我还有些反应不过来,几乎忘了刚才做过多么可怕的事。
我没有把廖青阳的死告诉任何人,足足请了三天的假,去学校时高维希还没燃尽对这件事的热情,一下课就来找我说话。
他问我:“易子,廖青阳为什么要杀那些人?他和你说过原因么?”
我本来准备摇头,想了想却说:“也许……是觉得寂寞,想让那些人陪他吧。”
高维希不相信地道:“怎么可能!他想让人陪也应该是杀你才对!”他突然发现自己说错话了,拍拍我的肩膀,满脸歉意地离开。
留下我在座位上发愣,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想过,廖青阳为他自己的“地下世界”考虑周全,甚至不惜把无辜的人拉进去,可他为什么放过我?是没把我当朋友还是他已经看出了我眼中的怯懦?
廖青阳不会回答我,再也没有人能够回答我。
几天以后我接到警方的电话,被问到一些关于“五月花”的事,我心里忐忑不安,担心他们发现了那个洞穴,然后找到廖青阳的尸体。不过还好他们并没有提到这个,只是告诉我,警方顺藤摸瓜得知了“五月花”的存在,经过调查发现,他们是一个结构严密的非法组织,开辟“地下世界”的初衷并不单纯,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这些曾经的“地行客”一有消息就通知警方。
挂了电话,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整件事情的发展是我始料未及的,似乎我和廖青阳从一开始进入地底就掉进了圈套,失去了重要的东西之后,竟然不知道失去的理由。
六
警方对公众封锁了“五月花”的消息,这件事也只是成为一则新奇的轶事。然而,每天都会有新的新闻,“地下世界”很快就被人们抛到了脑后,连着廖青阳这个名字,随着高考结束,再没有人提起。
我发挥正常,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轨道上。
只有我自己清楚那次的事情给我留下了什么影响——
比如看到下水道时会绕着走,不再靠近任何洞穴;
比如发呆过后,发现本子上涂满了大大小小的黑太阳;
比如我学会和别人保持距离,不再结交那么亲密的朋友;
再比如,我不再分享“秘密”,把那些年少时的故事深深埋在心底。
我没有再去看过廖青阳,“地行客”这个词已经离我很远,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忍不住会想,如果廖青阳带我去城郊那一次,我和他一起进去了,会是什么结果?或者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跟着高维希进入地下,又会是个什么结果?
但是这些思考毫无意义,廖青阳把他自己留在了地底,既然他不悔,我也没有立场指责。
“五月花”这个名字除了警方的档案,或许只有我还记着,廖青阳的脸时常在梦中出现,每次醒来,我都疯狂地想知道“五月花”的目的,无法控制的想法在脑中滋生——
如果没有“五月花”,廖青阳还会不会死?
“五月花”几乎成了我无法逃避的梦魇。
当初那个可笑的“秘密”,以及两个人的约定,说不清是他先走错,还是我先逃离,结果都只剩下一个人,不管是在地上的那一个,还是在地下的那一个,越陷越深,已经无法挽回。
直到现在回忆起,我才知道,“年少轻狂”这几个字,原来那么沉重,有人为它摔了跟头,有人为它吃了苦头,有人为它失去了重要的朋友,有人为他丢了一条宝贵的命。
作为回忆的资本,常常让人痛彻心扉。
微恐悬疑小故事合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茅山传说
- 简介:他死里逃生,却结缘茅山,不爱钱财,却富可敌国。茅山派机密、上海滩教父杜月笙发迹之谜、慈禧太后墓葬被盗之谜、僵尸、女鬼、黑降门降头术、道家斗法、未解之谜……层出不穷。一位位知己红颜,有的成为陌路,有的伴随左右,谁会笑到最后?主角吴志远,带你揭秘一段段惊险离奇、不为人知的神秘往事…………………………………………………………………………………………………………本书茅山法术描述细致,风水学理论深入其中,可读性极高。欢迎书友加群讨论,本书讨论群:362352291声明:切勿练习本书中一切道术、蛊术及其他法术。喜欢本书的朋友请收藏。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44.9万字6年前
- 怪物少女与侦探先生
- 曾经踏遍无数恐怖世界的强者的我,因为任务失败,最后变成了身上能长出触手的少女。于是我不得不同无用的侦探先生一起展开了降SAN值的旅程?
- 48.3万字5年前
- 穿越龙王传说之变成霍雨浩
- 简介:这个是穿越绝世唐门的第二季,主要讲述的是创世神霍雨浩因为混沌神的传承神位的考试被时空乱流卷入一个和他那个世界一样的平行在这个世界中,他又将如何,请看小说
- 7.6万字5年前
- 十二星座之死亡游戏(魔法)
- 简介:十二星座的继承者将互相厮杀,只有一人能活下来。会有十二个帮手,但如果没有战斗的念头会被帮手杀掉。十二星座继承者该如何做?真的没有办法能让所有人活下来?真的要杀人吗?
- 0.4万字5年前
- 无常鬼使
-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遇无常万事休。范天九原本只是个高考扼腕,准备就业的高中生,可忽然有一天收到封恐怖而诡异的黑色录取通知书,当他来到这个学校后才知道,这是一间专门培养阴间警察——黑白无常的专科学校。自此,范天九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开始学习勾魂,捉鬼,驱邪,并把一切不属于阳间的东西扔回黄泉去。
- 15.9万字5年前
- 西沙异闻
- 点过万骷灯塔,逛过百蛊鬼窟,翻过云顶蛇宫,下过西沙鬼窑!一个碎片、一张图,揭开尘封七十年的秘密!
- 5.0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