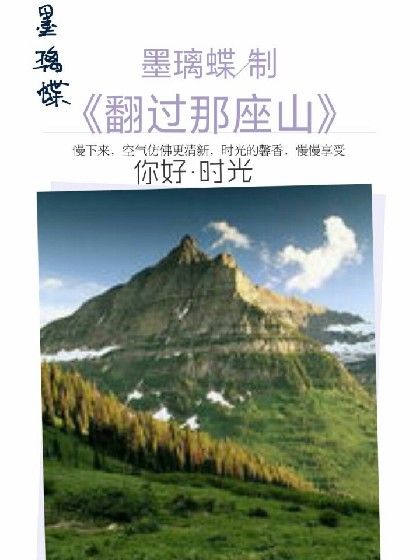1. 偶数
这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只有一所中学,高中部只有一个班。
刚搬来的时候,班级里有三十九个学生,加上我正好凑够四十人,父亲对此很满意。半个月前有个倒霉蛋在回家的路上被车撞死了,从此我就失去了上学的权力。
父亲认为这是为我好,他继承了母亲的怪癖,并发扬光大。
母亲有个坚守了一辈子的经典理论:物理学家都在胡扯,三角形其实最不稳定。比如两个人谈话的流畅程度永远最高,再掺和进一个,就会大打折扣。想解决这种情况,要么等第四个人出现,凑够双双互聊的局面,要么就请多余的那位离开。
同理,一群人加起来如果是偶数,才能符合成双成对的条件,否则总会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处处受排挤。
“你不觉得自己单独坐一张课桌非常尴尬吗?”父亲说,“还是在家自习吧。”
无所谓,我本来是重点高中的尖子生,自己看书本比老师反复讲解基础知识更有效率。
父亲决定搬家,是在妹妹离家出走后。
那丫头比我小一岁,心理年龄却成熟得异乎寻常。初中三年,她离家出走的次数用手指已经算不过来,但每次都超不过两周,直到中考落榜后才开始玩真的。
她留了封信,声称是追随真爱,奔向幸福。
父亲没有报警,等了四个月,决定搬家。母亲的失踪给他造成巨大伤痛之余,也增加了免疫力。我反对他这么做,但毫无效果。
他雇了辆卡车,载上全部家当,从市区出发,翻山越岭开了五个多小时,来到这处穷乡僻壤。指着黑色平原上像是仓库般的大木屋。
中间的二层楼有七八米高,靠北的屋顶有一间凸起的阁楼,两间硕大的仓库立在正房左右。木屋四周环绕着栅栏,附近别说住户,连棵树都没有。
这是祖父以前住过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冷冰冰的,毫无亲近感。
我似乎应该反抗,或是效仿妹妹离家出走,但我没有。因为犯不着在高考前夕闹独立,反正父亲已经承诺,只要我考上大学,随便去哪里都可以。
父亲的承诺并非信口开河。凭借木工手艺赚的钱足够吃喝,他还利用闲暇,在两侧的仓库里养了很多肉鸡,还算有些额外收入。
这所木屋是完全对称的,里边所有的设备全都是偶数:卧室厨房厕所仓库全都是两间,客厅也被劈成两半。
饭碗和菜碟被父亲用铆钉结合起来,这给端饭碗增加了难度,所以我经常把饭菜拌在一起吃。
我正在吃的是鸡肉,今早它的一个伙伴被野狗咬伤,惊慌失措地不知道躲到了哪里去,父亲拎着斧子出去了很久回来后告诉我,他收拾了那条野狗。遍寻不到失踪的鸡,便又杀了一只,鸡还是偶数。
父亲用线把两条鸡腿缝在了一起,被水煮过后紧紧粘连,像是个外星物种。不过我早已习惯了,毫无顾忌地咬下去。
他向来不愿意和我同时吃饭,因为就算鸡可以切成两半,但我的胃口没他那么好,总会剩下些,比如一个翅膀,一个爪子,于是他索性把所有成双的东西凑成对,订下了自助餐般的规矩:量力而行,不许剩下。
我勉强吃掉它们,吐出骨头。骨头被我啃得很干净,在白炽灯下散发出青色的光芒。我盯着这对左右对称的玩意,想到了母亲的一个理论。
她认为人类本身就是由偶数组成的:二百零六块骨骼,二十八到三十二颗牙齿,两只眼睛,两个耳朵,鼻子虽然只有一个,却有两个洞。
心肺胃脾肾要么成双成对,要么左右对称,这种理论虽然比较强词夺理,但也没法彻底否认。
“嘴怎么算?”我问?
“人人都有两张嘴。”她回答,“一张说真话,一张说假话。”
我想到了妹妹。她是母亲的影子,从小寸步不离。母亲失踪后,她变得魂不守舍,对我和父亲,总是刻意保持距离。父亲对她越好,她的脾气越糟。
儿子跟随父亲,女儿陪伴母亲,这种常见的家庭关系模式,在没有了母亲的情况下陡然失衡,偶数变成了奇数。她显得很孤单,却又拒绝向我们靠近,对任何人都非常苛刻,包括她自己。
她想寻找一个同伴,找到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我叹了口气,收拾好餐具,外边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这时有人敲门。
一个女孩穿了件闪闪发亮的黑色雨衣,低头站在那里,向我展开一只手掌。
“偶数!”她大声说。
“什么?”我困惑地问,“你找谁?”
她抬起头,露出一张憔悴的脸,不过还没有憔悴到让我认不出她。
“是你?”我惊讶的瞪大眼。
“偶——数!”妹妹重复道,露出白痴般的笑容,开始数手指,“一、二、三、四,五……五?!”
当时父亲读完她的告别信,用火烧掉,告诉我妹妹迟早会回来,疯疯癫癫的回来。我以为这是诅咒,绝没想到成了真。
我想把她拉进来,她拼命反抗,“五五五”地重复个没完没了,声音凄厉,宛如鬼哭狼嚎。我听得发瘆,粗声粗气地吼了一嗓子:“还有另一只手呢!”
她恍然大悟,用另一只手攥住小指,使劲向后一掰。
我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她疼得满头大汗,却笑靥如花:“一、二、三,四……偶数!”
微恐悬疑小故事合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盗墓传人
- 简介:墓之品,封山卸岭;虎头棺,煞气威胁。深入地灵殿,妖邪鬼祟生。邪武灵器成,算相挂位冥。
- 4.1万字6年前
- 翻过那座山
- 简介:讲的是一个老和尚收留了一个孤儿,带他一起去找寺庙打败恶龙的故事
- 0.3万字6年前
- 我的小说不可能这么正经
- 女儿天下第一
- 1.1万字5年前
- 十二星坟
- 一个恐怖的群聊,群聊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想逃吗?”“那就逃吧!”“不管你逃到哪,都是徒劳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0.0万字5年前
- 神探少女叶雨雯
- 少女叶雨雯以为一次偶然事件的侦破而被人们熟知,但因为她侦破案件越多就威胁了一部分黑暗势力,危险已向她逼近。
- 1.1万字5年前
- 她比亡灵还恐怖
- 简介:你听过午夜敲响的钟声吗?你看过菜刀女砍人吗?你玩过真正的捉迷藏吗?闭上眼,你看到的将是鬼魂们跪着叫你爸爸
- 5.2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