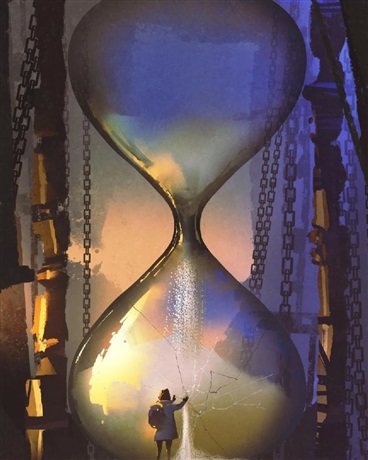第十六章 海边的旧灯塔
亚历山大走进帐篷时,第七猎骑兵团的军官全都安静了下来。
“抱歉打扰你们。”他对桌边的众人略一点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非常好,坏消息非常坏。”他看向我,“你想先听哪个?”
“好消息。”
“我们在马尔格雷夫堡的失败让国民议会非常不满。”亚历山大静静地说。“他们派来了几名代表,决定调查这次失败的原因。”
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好消息。“坏消息呢?”我用轻快的声音问道。
“为首的代表是洛郎将军的父亲。”
我深吸一口气,眯眼看着亚历山大,感觉自己被耍了。
“当父亲的会为了履行职责,收拾自己的儿子吗?”乌瑟中尉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
“我哪知道?我看起来像已经当上父亲的人吗?”我烦躁地回道,一边揉着隐隐作痛的太阳穴。“天哪,亚历山大,我做错了。我不该弄走卡尔托的。他虽然是个无能之辈,好色之徒,但至少不会帮倒忙。”
“那就把洛郎也弄走。”奥柏建议。
只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啊!从马尔格雷夫堡返回的当晚,我便再次向父亲打起了小报告。“我要的,是经验丰富,久经沙场,具备出色指挥能力的司令。您却给我送来一个只会在关键时刻添乱的猪头。”信的开头如是写道。信中还讲述了明明已经胜利在望,最后却功亏一篑的不甘。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父亲那边并没有任何回音。
众人纷纷散去之后,我将亚历山大送出营地。
“马库斯,我觉得自己会在下一场战斗中死掉。”周围只剩我们两人时,他唐突地说。
我也有相同的感觉。我差点脱口而出,但及时克制住了自己。“骑上那匹小肥马,跑回你的营区,再恶补一觉,你就不会有这种荒唐的错觉了。”我故作轻松地答道。人可以害怕,但必须知道何时该隐藏自己的恐惧。
亚历山大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会照你说的试试看。”他优雅地翻身上马,渐渐消失在清冷的夜色中。
目送亚历山大离开后,我穿过已经已然陷入沉寂的营地,来到伤兵居住的帐篷。一名女护士正提着盏灯在病床间轻轻走动。
“谁?”她用耳语般轻细的声音问。
“我。”我用同样微弱的声音答道。
“你是谁?”护士的声音有些不耐烦。她蹑手蹑脚地走近,将手中的灯凑近我的脸。“团长!伤员们都休息了,您来干嘛?”
“我来看看迪昂上尉。”我后退一步,以躲避刺眼的灯光。“他怎么样了。”
“他现在需要休息。”
“他都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了。”我低声说。“我们已经三天没见面了,我都快想死他了。”
护士哼了一声,尽管光线很暗,但我知道她此刻肯定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请您不要待太久,更不要惊醒其他伤员。”
“遵命,把灯给我。。”我从她手中接过这个昏暗的大帐篷中唯一的光源,小心翼翼走到迪昂的床边。护士走出帐篷,脚步轻得像只猫。
我用灯照亮迪昂毫无血色的脸。“你死了吗?迪昂?”
迪昂的双眼缓缓睁开,随后又在强光下眯起。“您就是这么问候伤员的?”
“抱歉,抱歉。”我缓缓地在床边坐下。“军营里的一些老兵饱受战争摧残,早已忘记礼貌为何物。我也就有样学样了。你的伤口还疼吗?”
“疼,但更让我痛苦的是马尔格雷夫堡和土伦城还在英国人手里。”迪昂把身子往上挪了挪。“我们差一点就能成功的,却不得不在关键时刻撤退……”他的伤口似乎痛了起来,没继续往下说。
“是啊!”我并不想过度刺激他,便随口编了个瞎话。“我们当时只顾眼前的阵地,却被英国人的骑兵抄了后路,不得不撤退,真是可恶。”
“为什么其他人告诉我的版本和您讲的大相径庭?”
我差点失手把灯摔碎。“大概是你这几天一直在昏迷,脑袋不清醒吧。”
“是吗?”
“迪昂,如果你死在我面前,我不会下令撤退。我会不顾一切向敌人冲锋,为你报仇,哪怕全军覆没也在所不惜。”我从床上站起,抬高手中的油灯。“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迪昂,你伤得很重,在土伦的围攻战结束前,都不可能再回到岗位了。而我……也许明天,我就会战死。所以,我想让你知道这些。现在,学弟,好好休息吧。”
该说的已经说了,我转身向帐篷外走去。
“团长。”迪昂在我身后低语道。“你变了。”
“是吗?”我停下脚步,看着黯淡的灯光照亮外衣的下摆。“是啊!在小停泊场的山坡上,我几乎就是个勇士;在马儿格雷夫堡附近的沙地上,我几乎就是个真正的军人。”但这并不能让我心中的恐惧消减分毫。
那名女护士就等在帐篷外面,就着皎洁的月光,我看清了她的容貌。她有一头垂至腰间的红发,蓝眼睛里带着责备的神色。空气中的寒意为她脸颊抹上了一层红晕,让她的面容更添神采。
“你叫什么名字?”我将油灯递还给她,问道。
“苏菲娜。”
“晚安,苏菲娜。”
“晚安,团长。”她微微行礼,转身离去。
之后的几天,大概是急于在自己父亲面前表现一番,洛郎将军下达了许多荒唐的命令。诸如在英军大炮可以打击到的地方修筑阵地;不顾一切地浪掷兵力,让士兵在敌人坚固的工事前白白送死,还撤掉了大批才能出众的军官。这些倒行逆施让我不禁怀疑这家伙其实是英国人派来的奸细。
巴黎来的代表们终于到达了前线,这一消息很快便在革命军的营地传开。
我独坐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对着已经冷掉的外餐,没有丝毫胃口。苏菲娜失魂落魄地走进来,她的眼睛红红的,似乎刚刚哭过。
“团长,我惶恐地向您报告。”她用沙哑的声音说。“一名伤员刚刚去世了。”
我感觉胃里像被人打了一拳,不由自主地握紧手中的餐刀。“谁死了。”
苏菲娜念出一个名字。他是一名性格孤僻的中队长,在小停泊场的战斗中被炮弹炸断了两腿。
不是迪昂,我大大地松了口气,紧绷的肌肉立时松弛下来。“太好了。”此话一出,我便后悔了。苏菲娜的眼神几乎可以把人吓死。“天啊,我已经悲痛逾亘,神志不清,口不择言了。麻烦你给我倒杯酒吧。”
护士冷着脸倒了杯酒,放在几乎被地图占满的桌子上。
我邀请她陪我喝几杯。起初苏菲娜强烈拒绝,但经过我再三请求,她终于答应坐下来喝一杯,暂时将伤员们交给自己的同事照料。她喝了不只一杯。接着,苏菲娜开始敞开心扉,向我谈起她无力救回的伤兵,谈起全心付出后却还是面临失败的沮丧,谈起抵御悲伤的艰难。我看着她,突然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在布里埃纳军校遇到的那名医生。
“死亡真的有那么遭吗?”我摇晃着手中的酒杯问道。
“您为什么这么问?”苏菲娜一脸惊愕。
另一个人的记忆在脑海中复苏。“以前,我去医院看自己的爷爷。他当时看起来很痛苦,当他看到我时,他还哭了。”时隔多年,再提起这件事,竟仍令我颇为感伤。“后来,在我朦胧的泪眼注视下,他的心脏不再跳动。当时我并没有像周围的人一样痛哭失声。”
“为什么?您不爱他?”
“我爱他。但当心电图归于直线的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终于不再痛苦了。他的生命已经离开了垂死的躯壳,获得了安息。永恒的宁静降临在他身上,也感触了我的心。难道不是吗?死亡与疯狂,与其说是生命的雷池,倒不如说是避难所。无论是你没能救回的那位伤员,还是我死去多年的爷爷,此刻都在享受着港湾里的风平浪静。可怜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需要面对命运掀起的狂风暴雨。”当红酒溅洒到地图上时,我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已经醉得很厉害了。“死亡,是大炮和职责都不能惊动分毫的安眠。让我们遥敬死神一杯吧!”
“您醉了,团长。”苏菲娜说。
这时,拿破仑走了进来。“上帝啊!马库斯,你醉得像条狗一样。洛郎将军举办了一场宴会欢迎国民议会的代表,你不知道吗?”
“狗!”我歪歪斜斜地站起身,步履蹒跚地走出帐篷。月如白练,高挂天空。我将双手拢在嘴边。“啊呜呜呜……”这不是狗的叫声,而是狼的。
“你疯了?”拿破仑跑到我身边。
“拿破仑,”我前跨一步,伸手抓住她的右肩,另一只手顺着她的大腿滑至细小的后腰。“我们一起对月长嚎,惊醒沉睡的上帝吧。”
她猛地将我推开。“你醉得太厉害了,还是别去参加宴会了。我会向洛郎将军解释的。”
“不,我要去。”我回答,“我必须去。”
奥柏很快便为我牵来坐骑。我笨拙地跨上马背,跟着拿破仑一起前往指挥部。寒风瑟瑟,令我混沌的脑袋清醒了一些。想到几分钟前的那一幕,我几乎当场失声尖叫。真是太丢人了!我记得在我学狼叫时,有十几名士兵就在旁边绕有兴味地看着。下次战斗得派他们打头阵……
拿破仑扶着我走进起居室时,宴会正要开始,美食和红酒占满了长桌。我在里昂身边坐下,只觉泫然欲呕。
国民议会派来的代表一共有五人,在这五人中,我一眼便认出了洛郎将军的老爸。他坐在全场最尊贵的位置上,模样和儿子非常相像,只是脸上有些皱纹,鬓角的灰发夹杂着银丝。
老洛郎举起酒杯,“各位,我听犬子讲述了马尔格雷夫堡之战的经过。”他朗声说,“这次的失败,与在座列位断然无关。”
没错,这事全怪你那不争气的儿子,赶紧让他背着这口大黑锅回家哭鼻子去吧。我趴在桌子上,心中暗忖。
“此次失败,皆因驻扎在马尔格雷夫堡正面的部队,也就是马丁少校所率第三十一步兵团中的个别士兵,无视军令,擅自冲锋,才会酿成大祸,连累全军。”这位代表续道。
“父亲,我已经下令严查,一定会把这些害群之马揪出来,让他们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代价。”洛郎将军郑重其事地说,“另外,我还要追究马丁少校治军不严的责任。”
餐桌对面,满脸络腮胡的马丁少校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这父子俩还在一唱一和时,菲利普搅和了进来,大鼻子下挂着谄媚的微笑。“代表阁下,在马尔格雷夫堡的战斗中,洛郎将军亲自带领少数随从挺身危地,鼓舞士气,在他的指挥下,全军才得以有序撤退,并未蒙受过大的损失。”
靠,要不要脸了?我只觉一阵恶心。
“马库斯,快坐起来。那几名代表一直在看着你。”里昂推着我的肩膀说。
“让他们看。”我回道。
又一名军官开口了。“洛郎将军虽然年轻,但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他已经成功证明了自己是个称职的指挥官。”
这时,我很应景地吐了起来。由于没怎么吃东西,吐出来的只有红酒。有人拍着我的背,应该是里昂。我用手背抹去嘴角的酒渍,接着,蓦地,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笑声平息,我缓缓挺起胸膛。“洛郎将军证明了自己不适合当一名军人。”
“你说什么?”总司令红着脸嚷道。
“他毫无指挥才能,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懦夫。他让成百上千的法国军人白白牺牲,他让唾手可得的胜利变成了失败。”
“你再敢说一句诽谤的话。”洛郎将军唾沫横飞地叫道。“就别想继续在军中待下去了。”
他的老爸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用那双冰冷的黑眼睛注视着我。父亲的沉默比儿子的威胁可怕百倍。
“诽谤吗?”我轻轻吐出这几个字。迪昂的身影在脑海中浮现,在他身后,站在苏菲娜无力救回的伤兵。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在众人的注视下摇摇晃晃地站起身。长桌上坐满了军官。“各位,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长官是什么货色。他永远也不可能带领我们夺回土伦城。”
没人说话,没人响应。里昂猛拉着我的袖子。我甩开他的抓握,沿着长桌缓缓踱步。“马丁少校,我有幸与您的部下在克尔海角并肩作战,他们都非常的英勇。他们成功占领了克尔海角,正要扩大战果时……”
“他们的行为是抗命,并且招致了失败。”马丁打断我的话,低头看着面前的酒杯。
我苦笑了几声,看向另一名军官。“泰格少校,您的军队一度冲到战场最前面,从背后逼近了马尔格雷夫堡。如果洛郎将军没有因为身边的副官阵亡就下令撤退,那么现在驻扎在那一战略要地的就是法国士兵了。”
“是吗?”发问的是洛郎将军的父亲。
泰格少校灌下一口酒。“未必。”
我在一名年迈的中校面前停住脚步。那位老人一言不发地别过头。我知道没必要再对他说什么了,于是继续往前走,心如刀绞。
在这个弥漫着红酒芬芳的起居室内,一共坐着不下二十名法国军官,其中三个还是我的挚友。可不知怎地,不知怎地,我竟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
亚历山大用那双总是波澜不惊的碧眼凝视着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我不理会他的暗示,将目光转向了拿破仑。“拿破仑。”
拿破仑轻轻叹了口气,垂下眼睛,没有说话,没有说话,没有说话。
“别试着去找同犯了,马库斯。”洛郎将军笑着说。“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我就不追究你这次的无礼了 。”
他的父亲站起身。“还有哪位先生觉得我儿的能力不足以胜任总司令一职?”
一片沉寂。
“27比1啊,马库斯少校。”
我望着这帮噤若寒蝉的同僚,他们的肩章在火光下熠熠生辉。“你们……”我觉得自己在做可怕的噩梦。“你们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军人吗?”我使尽全身力气,将面前餐桌整个推倒。血红的酒液和滚烫的汤汁溅到了军官和代表们华丽的衣服上,留下片片深渍。
拿破仑快步越过杯盘狼藉的地板,走到我身边,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酒醒了吗?”
这里只有我醉了?“这里只有我醒着。”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何等的,凄凉。我推开拿破仑,向门外跑去。
我没有返回营地,而是来到了海边的灯塔。夜色深沉,云层已将月亮完全遮蔽,这是个无星之夜,大海漆黑如墨,无边无际,带着一种诡异而深邃的美。我注视得越久,便越想投身其中。如果天气不是这么冷的话,我可能早就这么做了。
身后传来碎石响动。“谁?”我哑着嗓子问。
“我。”这是拿破仑的声音。
“谁是我?”
“这是什么蠢问题?”她轻笑着走上前,坐到我旁边。“大家都在找你,但只有我猜到你会在这,在这座我们曾一起眺望大海的灯塔。”
我没有回答,透过斗篷的兜帽,传来海风的低语。
“还在难过吗?”拿破仑问。
“我心犹如这倾颓的灯塔。”
“你在作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如果我作诗,你会听到这种押韵对句的诗。”
“你真的很有天赋呢!”拿破仑忍俊不禁,“回去吧,这里冷死了。”
“冷大莫过于心寒。”
拿破仑苦笑了一下。“你在生我的气?”
“我当然在生气。”我一字一顿地说。“拿破仑,我以为你是一只狮子,但现在我才发现,你是一只绵羊,你是一群绵羊中的一只。”
“咩咩。”她轻声学起了羊叫,接着发出清脆的笑声。“我有时是狮子,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绵羊。智慧就在于根据不同的场合随机应变。”
我突然觉得她变得好陌生。两人明明离得如此之近,距离却在缓缓拉开。“走开,拿破仑。”
她缓缓叹了口气,“马库斯,我们都不再是军校里的孩子了。你该明白,这个世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正义和单纯。有些事情仅凭热情和努力是做不到的。尤其是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人们很可能会因为片言之失被送上断头台。你从小就生活在自己父亲的庇护下,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纵容你,所以……”
“所以我有棵方便乘凉的大树?”我尖刻地反问。“所以我永远都只能活在父辈投下的巨大影子里。”
片刻的沉默降临在这座灯塔。
“对不起,我这次没能为你站出来。”最后,拿破仑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你应该也看出来了,那场宴会不过是做样子,洛郎将军的父亲在巴黎堪称权势滔天,与会的绵羊们若不咩咩叫着支持那位废物司令,很可能会被革职,甚至更惨……”
这时,我的酒已经醒得差不多了,大脑逐渐恢复了思考的能力。“说实话,拿破仑。我有些后悔掀桌子了。”
“别担心,马库斯。”拿破仑将手滑进我的发间,“你会没事的。”这时,月亮自云层后现身,皎洁的月光倾泻而下。她瀑布般的长发被射入灯塔的苍光濡湿。
“少校!”我看到她的肩章后,脱口而出。“就因为你打了我一巴掌,他们把你升为少校?”
拿破仑露齿而笑。“不是因为我打你的那一巴掌,而是因为我脑门充血时给洛郎将军的那一拳。”
“啊?”我完全没听明白。
“当时他威胁要报复我,现在他开始行动了。”拿破仑笑意未消。“下次进攻我们很可能会再次大败亏输。这样一来巴黎军事当局会非常不满。”
一阵寒意爬上我的脊背。“所以需要杀一只替罪羊来平息众人的怒火,就像伊斯兰教的宰牲节。”
“没错,而比起处决小小的上尉,杀一个少校会更令巴黎方面满意。”她看向夜色中翻涌的大海。“半个小时前,当洛郎将军面带微笑地将少校肩章为我佩在身上时,我就猜到了这点。”
“那你还有心情来找我?”
“放心,马库斯。”她用那双澄澈的双眸看向我,月光正在她眼中栖息。“我不会被处决的。身为共和国的军人,我不会那么死。”她缓缓地站起身,在狭窄的旧灯塔中投出巨人般的影子。“在战场上,我永远都是狮子。我会像狮子那样死去。”
“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也站了起来。两人的吐息在冰冷的空气中交融。“我发誓,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与拿破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灭实录
- 万民原本只想做一个五好公民,直到某一天,他坐在家里,祸从天降……从此,他走上了复国之旅。
- 17.3万字5年前
- 异能哥哥与天才少女
- 一直希望有个妹妹的骁寒,在高一开学的那天突然接到父亲的通知,自己竟然是许久未见的母亲与妹妹在医院???但这背后却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 5.8万字5年前
- 从零开始的莫比斯环的赠礼
- 汝莫要行偷窃之事届时吾会亲自了断你
- 1.5万字5年前
- 真实之人
- 上帝创造了人类,人类创造了我们,为什么人类能怀疑上帝,而我们却不能怀疑人类。——智能人形Z023PS:本对话为短篇,也是作者唯一写了大纲的小说。
- 0.0万字5年前
- 传说世界的超武
- 传说世界中的超武,潜藏在“深度之海”中的秘密。
- 12.6万字5年前
- 这只是幻想请不要介意
- 这只是幻想请不要介意~~如果大家能有所感触,作者的内心也会很温暖世界的强大,你我不能轻易感触世界的温柔,其实无所不在世界的宏伟,使我们哭泣震撼请和作者一起徜徉在幻想的海洋之中吧谢谢你们的陪伴
- 2.6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