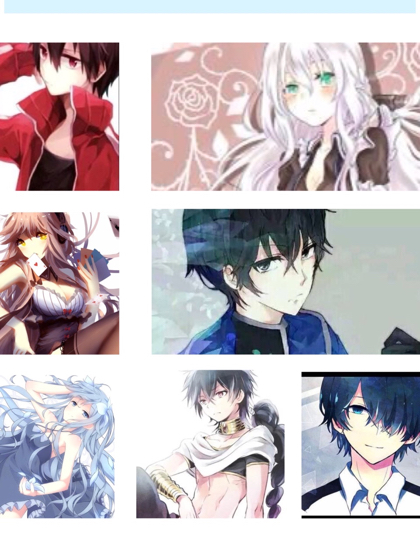Chapter 15.卡桑卓尔
第三次在棋盘上输得一塌涂地之后,塞维克斯宣布:“我要出去吹吹风。”
“去吧。”卡桑卓尔微微一笑,朝梅丽娅招手,示意她过来收拾。黑发少年跳下椅子,像模像样地捋了捋外袍的衣领。这是杰卡利亚从座椅上起身后的惯有动作,他学得还挺像。随后,黑雾弥散开来。“我不喜欢下棋。”他变成黑鸦前说道,接着拍打羽翼,飞出窗户。
梅丽娅将玛瑙棋子一只一只收入六边形木盒。“哈里克带着大部分护卫进了宫,塞维克斯又这般擅自离开,您也许会有危险。”
“能有什么危险?”卡桑卓尔道,瞥了一眼自己的女学徒,“我不过是一介小小侍官,身体里流淌的乃是埃斯洛特史上最声名狼藉的血统,还不得主君的宠爱——谁会在乎?”她边说边脱掉靴子,在软榻上躺了下来。“把棋收好以后,麻烦给我取些酒来。”
“龙血酒?”得到肯定的答复,梅丽娅长叹一声,“我知道我不该多嘴,老师,但……但您最近喝得实在是有些过量了。殿下不会喜欢您这样的。”
“他喜欢的那个我早就死在安克沃家的塔楼里了。”她自嘲一笑,“现在的我不过是具空壳。冷冰冰的,总得找点东西暖身子啊。”
梅丽娅面露难色,但还是取来了她要的烈酒。两杯下肚,卡桑卓尔便感觉自己血管里流的是滚滚岩浆。“你杵在旁边干什么?坐下来陪我一起喝。”
“抱歉,我喝不了这么烈的酒,老师。”
卡桑卓尔摆了摆手,“那就出去,让我一个人待着。”
女学徒娴静有礼地告退。门扉关闭的一刹那,仿佛整个世界都已消失,于是她仰起头,喝掉第三杯。龙血酒最大的好处就是奇妙的眩晕感,强烈的头痛以及血液在肌肤下燃烧的错觉,任何情绪都会被这些刺激焚烧殆尽,像龙焰掠过平原那样,烧得一寸不剩。
但野草总会再次钻出地面,那种要将人整个撕碎的绝望感也会重新袭来。也许是伊西的气候对埃斯洛特人来说太过严酷,也许是过于劳累,也许是厨师的手艺变得越来越不合口味……各种原因纠缠在一起,无法理清。酒壶见底后,卡桑卓尔垂下眼帘,随手将杯子一扔。镶银的酒杯撞上墙壁,然后坠落,发出痛快的声响。她闭上眼睛,不消片刻便回到记忆中那座恐怖的塔楼。
那时她被新婚丈夫锁在塔楼最高处的冰冷房间,唯一的衣物是一条粗糙的毛毯。每天红月升降时,家奴会送来一小块干硬的面饼和一壶清水。安克沃害怕家奴被她的言语蛊惑,因此每次派的人都不同。他自己却每夜准时前来**她,并且时常伴随着殴打。起初她尚有力气反抗,但是不出两个星期,她就虚弱得连站立都困难。痛苦,恐惧和绝望紧紧绞在一起,凝成一根勒住她颈部的铁索,然而安克沃不准她死。他声称只要她生下儿子就会放过她,她却知道自己这幅半死不活的身体即使怀了孕也只会流产。
房间有一扇窗户,她勉强爬得上去。窗户外面是无尽夜空和绵延不绝的深紫山峦,下方则是坚硬的石板地——只需片刻的勇气,即可获得永久的解脱。清醒的时候,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呆坐在窗前,面对一成不变的景色,等待那片刻的勇气涌上心头,但每一次都以安克沃的开门声告终……痛苦和幻觉模糊了她对时间的感知。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从外面打开门的不再是可怕的丈夫,而是一个似曾相识却又无比陌生的身影。直到他出声,卡桑卓尔方才确定他是谁。记忆的尾声,是一双有力的手臂,冲天的火光以及塔楼坍塌亦无法掩盖的哀嚎。那是令她永生难以忘怀的景象,亦是第一次真正领略所谓“毁灭之意志”是为何物。天山一色的绯红,纷纷落雪消融成雨,一切都在烈焰中扭曲变形,燃烧殆尽。
一阵寒意忽然袭来。她摸索着从软榻上起身,结果眼前天旋地转,烛光变成了黑白。她再度睁眼时,已经趴在了地上。今天喝得太急,她一边责怪自己一边站起来。“梅丽娅?”
无人回应。
卡桑卓尔缩紧肩膀,“梅丽娅?”
这不是寒意,而是不安——她猛然意识到,不知从何时起,除了她的呼吸,四周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声音。她深知房间的隔音没有这么优异,如果并非何人在暗中摆弄法术或者恶作剧,剩下的解释就只有……
卡桑卓尔吹熄桌上的蜡烛,然后将剩余的半截白蜡拔掉。黄铜制成的烛台尖锐而锋利,只要刺得准,可以成为致命武器。她尽可能不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口,然后轻推门扉,另一侧立刻传来硬物磕碰发出的声响。门从外面栓上了。
很好,卡桑卓尔皱起眉头,起码不会有人从这里进来。她转过身,房内依然灯火通明。我该把剩余的蜡烛也熄了,然后找个地方藏身,假如对方是手持利刃的杀手,这样或许有用。但如果是伊西人的法师,熄灭蜡烛无异于自掘坟墓。他们的法术无法染指尊贵的他所在城市的火焰,因此也无法侵入这个房间……至少理应如此。
然而寒风叫她浑身发冷——窗户的其中一扇是开着的。
她看到深红窗帘随风鼓起,一只蜡白色的手撩起帘布。
“你不需要举着烛台。”
卡桑卓尔不打算放下仅有的武器,尽管她知道若真动起手来,自己必死无疑。
这名陌生人比护卫队长哈里克还高出一头,身躯修长而健壮,斗篷和靴子漆黑陈旧,但那柄尚未出鞘的剑单看白与金交织的剑柄就知绝非出自寻常铁匠之手。
对方步步逼近,她则步步后退,直至后背抵上门板。
“你是什么人?受谁雇佣?”
陌生人在距离她五步远处站定,以四大王国的通用语回答:
“以剑刃侍奉圣主之人。”
卡桑卓尔不由屏息。
“安格罗,对吗?那是教会给你取的名字。他们可曾告诉过你我们的母亲死后受到的是何种礼待?”
同母异父的弟弟以沉默作答。他的长相和她预料中相去不远,特别是高挺纤细的鼻梁、冰冷生硬的面部轮廓以及紧闭的细薄嘴唇。但她没想到这些特征被一个男人拥有时看起来会如此顺眼。克尼克斯男人以缺乏男子气概闻名于世,然而他的另一半血统完美地弥补了这个缺点,尤其是仿佛能够承受一个世界之重的宽阔肩膀。那双眼睛虽一银一蓝,透出的冰冷和忧郁竟有几分像母亲。
“你不应该长得这么像赫里斯家的人,”弟弟的相貌唤醒了她心底的伤痛,“你那可恶的父亲夺走了我唯一的亲人。出征前夜她向我保证她会回来,回到诺尔安特。我等了十六年,等到的却只有她的死讯和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他静静地注视着她,依旧面无表情。她不知道这是训练有成的掩饰还是饱经沧桑的麻木。
“我不知道。我也从未听过她叫我的名字,从未亲眼看过她的面容。我听说你和她长得很像……但没听说你有酗酒的习惯。”
“你这混种没资格教训我。”
他过了一小会儿才继续说道:“我本想和你谈谈,可惜你现在并不适合交流。”
说罢,他转身就走,这行为让仍举着烛台严阵以待的卡桑卓尔顿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该把这玩意刺进他后脑勺,她心想。
“给我站住!你来伊西做什么?”
青年顿住脚步,稍稍侧身。“取你主君首级。”
“天真。”卡桑卓尔笑了,“想当英雄,只凭一把剑可远远不够。”
“这把剑曾斩下‘魔皇’的右臂。”
“然而挥剑的却不是同一人。”
在打嘴仗这方面,异父的弟弟显然不是她的对手。但他应该没有说谎,那把剑是真品,是“圣子”对他七位骑士的馈赠。至白至圣的力量流转于剑刃的寒光之中,能够切断任何黑暗起源的法术。自己虽然并非夜司书,身体里的血却也能感受到那种威胁。弟弟虽是圣徒,但赫里斯的血脉不会因为信仰而改变,因此理论上而言,他不仅无法完全发挥出这柄剑的威力,还要为此忍受折磨。此刻,剑刃尚未出鞘,只是离得足够近,卡桑卓尔便感觉到肌肤下的血流中好似生出了荆棘。
她还在奋力思索如何利用眼下的情况套出更多有用的情报时,巨响从门外传来,似乎有人用攻城锤撞碎了一面玻璃做的墙壁。随后房门开启,走进的人一身绯红,俊美脸庞因怒意和嘲讽而扭曲。紧随其后的还有以哈里克为首的十名亲卫,个个手执长枪和盾牌,将她前方组成阵型。
“设下‘御界’然后带着剑闯进女人的房间,拥有你这样的战士圣主想必非常荣幸。”
安格罗以防御的姿态持剑而立,冰冷面容丝毫不为王子的话语所动。
下一刻,点点烛光升起,变成游弋的火星,然后瞬间凝为嘶叫的火蛇扑向圣徒。青年向前半步,拔剑与挥砍一气呵成,动作快到卡桑卓尔看不清,唯有剑刃出鞘的时刻,血液里的刺疼变得更为猛烈。火蛇碎裂成三段,变作青烟飘向屋顶,剑士则毫发无伤。王子打了个响指。火焰监牢凭空浮现,将他困在其中,他则立即将剑刃的光辉凝于一处,强行破开牢笼。白光刺得卡桑卓尔眼睛发痛,甚至一度以为自己要失明。
待她再度睁眼,安格罗已经不见了踪影。
“哼,逃得倒快。”杰卡利亚转过身,相当随意地作了个手势,示意亲卫们退下。“你怎样?有没有受伤?”
卡桑卓尔摇头。“他还会再来的。”
“吓到了?”
“没有,只是……”
眩晕袭来,卡桑卓尔捂住额头,然而身体不听使唤地朝前倒去。杰卡利亚阻止她前倾的同时顺势将她抱了起来。
“你今晚到底喝了多少酒?”
头顶响起的声音无奈多于不满。卡桑卓尔伸手攥住他的衣襟。“梅丽娅,还有……”
“其他人都没事,”王子边走边说,“这帮废物根本没发现有人潜入,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还一脸蠢样地瞅着我。”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她迷迷糊糊地问。
“如果我是他,今晚我也会来找你。”
但你还是出席了伊西王宫的宴会……和阿芙洛狄亚一起,她咬着嘴唇想。
走廊里忽明忽暗的灯火在她眼中变为模糊的橙红影子。总有一天他也会这样抱着那个女人穿过长廊,很快——凡人生命短暂,然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便再也无法寻回,到那时漫长的生命将会变为世上最可怕的刑罚。或许有人生来注定一无所有,生来就要看着自己珍视的一切被命运夺走,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正如她预料,王子将她抱回了自己卧室的大床,还亲手解开她盘起的长发。发觉她身体绷紧便轻声笑道:“别紧张,好好休息。”
“我不是在担心。”虽然我在担心另一件事,但那件事无论担心与否,结果大概都不会改变。“宴会怎样?”
“不怎么样。”杰卡利亚轻轻捻着她的发梢,“给阿芙拉顶罪的是个侍女,年纪不大。小国王想活活烧死她,但被我抢先一步,所以没受什么苦。”
凡人在他的火焰里撑不过一秒。纵使可怜,她仍遗憾没能亲眼目睹,心底竟然还有几分令自己惊异的嫉妒。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样辉煌的橙红里终结。如果能挑选自己的死法,比起孤独终老或纵身一跃,她更愿意死在这双绯红眼眸的凝视下,化为灰烬,不给任何人羞辱自己遗体的机会。而且,还能将自己最后的模样映在他中。
低着头的王子没有看到她嘴角浮起的自嘲笑意,仍专心致志地把玩着她的头发。克尼克斯人生来都是黑发,但大多偏向深蓝或是墨绿,有些还会泛紫,但她的发丝是最纯粹的黑,一如无边夜空。她记得有一次宴会上,一个瓦古安家的旁系子弟经过她身边时,忍不住摸了一下她的发髻,却不幸被眼尖的杰卡利亚抓个正着。尚未成年的王子大发雷霆,命令亲卫当场砍掉了那个少年的右手。瓦古安家是承自“夜鸦王庭”的十三大贵族之一,无论朝野之上还是夜都之中都颇有势力,此举险些引发王室与大贵族之间的战争。所幸被砍的男孩在家中地位很低,母亲不过是个舞娘,加上卡桑卓尔的血统早已变成祸国的同义词,事态才没有继续恶化。不过即使事后了解到可能引发的巨大危机,王子也没有流露出半分悔意,还高傲地向皇后表示就算对方是瓦古安家的直系,他也会照砍不误。
记忆虽久远,如今忆起却仍倍觉甜蜜,并且滋生出一种突如其来的疯狂。卡桑卓尔拉过王子的手,让他握住束腰的墨绿绸带。
“我想要你。”她喃喃轻语。
那张能令红月黯淡无光的俊美面容被片刻的惊异占据,随后,比烈酒更醉人的笑容浮现上来。他慢慢俯身,直到两人的脸庞近在咫尺。
“我没听清,再说一次。”
她没有服从,直接伸出手臂揽住青年后颈,舌尖探进他张开的唇。他开始除她的衣裙,先是束腰,然后是从领口延伸至胸前的一排纽扣。她感觉到自己的肌肤一寸寸暴露,滚烫的亲吻和爱抚则一寸寸紧随,然而这样被动地享受无法释放血液里的压抑。于是她挺起脊背,撕开他的长袍,将他修长优美的身体向后推去,像训练有素的妓女一样骑到他身上,用尽全力扭动腰际。随着身体的起伏,她的名字在他唇边渐渐化为毫无意义的呻吟。她死死按着他的胸膛,像身中剧毒一般猛烈喘息,不愿去想是极致的痛苦变成了甜蜜的欢愉还是欢愉的极致变成了甜蜜的痛苦。
以往两人结合时,卡桑卓尔总是咬着自己的手背,不愿让任何下人听见,但醉酒的恍惚让她不屑于思索任何眼前以外的事物。从得知母亲背叛及死讯的那一天起,她就知道命运的别名是无情。一个女孩,失去了一切,还要独自背负家族的耻辱,独自承受来自世界的恶意,然而——幸运又不幸地——找到了世上最温暖的怀抱、笑容和吻……到最后,她的喘息化为尖叫,盖过他的声音。
尽管知道所有美好最终都会以最痛苦的方式湮灭,我仍想拥有你的全部,杰卡利亚。
她慢慢地翻过身,躺在他旁边。温热退却后,涌上来的是让她不得不闭上眼以免流泪的失落。如果这是最后一次……她一想便开始颤抖。
王子从后面抱住她。
“你最近有点反常,希望你没对我隐瞒什么。”
“没有……殿下。”
他撑起上身,“现在我又变回你的主君了?”
“您一直都是。”
“我不过是在关心你。是你这个人,不是我的女侍官,明白吗?”
卡桑卓尔将毯子拉过胸前。她当然明白。“谢谢您的关心。”
“如果你受不了伊西的气候,我可以让塞维送你回蛇岛——”
“不,”她差点喊出来,“我……臣女不能走,为了您的事业,不能……”
杰卡利亚盯着她,最后无奈地笑了。“也好,能亲眼看见你,我会安心些。不过,别趁我不在的时候一个人喝那么多酒,我需要冷静清醒的女侍官。”
“遵命。”她垂下眼帘应道。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睡吧。”
这一觉她睡得很沉,没做任何噩梦,将她唤醒的是穿透厚重棉绒帘幕的午后日光。大床上只有她自己,但床边置了一张银盆,一朵红莲漂浮其中,这是她主君的习惯。在蛇岛,她醒来时收到的是插在细长陶瓶中的蝎尾兰。房间另一侧,梅丽娅侍候在窗边,右手挽着一条藏蓝色新裙服。
“日安,老师。”她行礼道,“殿下命我等候您醒来。”
“他去哪儿了?”
“和哈里克一起到军营去了,好像是要增加些人手巡护这座宅院。临走之前殿下还训斥了塞维克斯一顿,他到现在还委屈呢。”
我不该在棋盘上欺负他,卡桑卓尔轻叹,但不知为何昨晚就是收不住手。“稍后请他和我一起用餐,如果他乐意的话。”
“是,我这就去安排。还有一件事,王宫内的眼线昨晚传来一个消息,但那时您……”梅丽娅顿了一下,脸颊泛红,“我不敢打搅,只好等到现在。”
“没关系,说吧。”
“昨晚宴会结束后,有人瞧见伊西的大学士希瓦多罗斯独自与阿芙洛狄亚会面,建议她和殿下联姻。”
卡桑卓尔翻身下床,“他知道吗?”
“还不知道。”
“希瓦多罗斯……可是那位很有名的学者?”
梅丽娅递上裙服。“是的。他名义上掌管着伊西及里亚学院和图书馆,但年事已高,日常事务不得不托付他人打点。阿芙洛狄亚是他的学生。”
“年事已高,脑子倒是转得不慢。”卡桑卓尔边穿衣服边说,“告诉塞维,天一黑就送他上路。”
女学徒伫在原地,满脸惊愕。“此话当真,老师?”
“若要小公主作我埃斯洛特的傀儡,就不能让她有别的依靠……哪怕只是提供建言也不行。”
“老师,希瓦多罗斯虽然没有实权,却也位列伊西朝臣之一,在贵族中颇有名望。您这样决定,会不会太草率了些?”
这身新裙子有点紧。卡桑卓尔系好扣子,坐到梳妆镜前。铜镜中的女人面色苍白,一脸残忍,恍惚间她甚至未能反应过来那是自己。
“你说得对,这样太草率了。”她抓起木梳,“殿下说我近来反常,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梅丽娅抿着嘴唇犹豫了一会儿。“被您挑中前,我曾跟家母学过几年医术。我想您可能是疲累过度。伊西的气候对埃斯洛特人来说不好受。哈里克手下也有几个人害了病,浑身无力,脾气暴躁。但您,或许……”
女学徒示意她抬头,然后手指覆上她颈侧,稍稍按压。
“怎样?”卡桑卓尔问道。
“和、和我猜测的一样,老师。”梅丽娅颤抖着说,“您怀孕了。”
破败王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失忆的我被病娇下属们拥举成王
- 为什么我一觉醒来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呢?身边还围绕着一群对着我流口水的漂亮女孩子,说是我的下属什么的……但是……为什么我感觉这些女孩子有些怪呢……似乎是……有点病态?宠溺型、排除型、缠扰型、依赖型、独占型、洗脑型、孤立引导型、自残型、杀..
- 58.4万字5年前
- 这个勇者不去打魔王却来攻略我
- 想要白给是不可能的!身为猫娘公主的我怎么可能这么随便就被勇者攻略啊!话说你这个勇者为什么不去打魔王啊!路过的大佬们来看一下哈,嫁人欢乐向,绝对不虐!稳定更新方向食用!另外十分抱歉的是因为还没有绑定手机号所以不能回复大家的评论实在是抱歉!
- 41.4万字5年前
- 代号:伤风
- 简介:他,龙海混血,手持剑戟审判天下;他,龙梦血脉,手持最终救赎天下;她,女子战士,与敌一战一统天下;他,继承血脉,成为魔神再兴天下!
- 2.3万字5年前
- 百鬼夜行之雪女物语
- 因神秘妹妹遗愿来到东瀛大陆,因为误食雪女心脏成为妖怪少女。成为她的他该如何抉择自己的人生呢。是成为百鬼之主,还是加入别人的百鬼夜行。且看雪女的一生的爱恨情仇。93318433
- 3.1万字5年前
- 还尘天地
- 简介:从正到邪,从魔到人,悟七情六欲,体人间寒霜。噬为噬,还尘是还尘。还尘是噬,噬即还尘。多道时间线的交汇,扯出亿万年前一块石头布下的古局
- 3.8万字3个月前
- 剑起风雷
- 剑起星奔万里诛,风雷时逐雨声粗。人头携处非人在,何事高吟过五湖。
- 2.0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