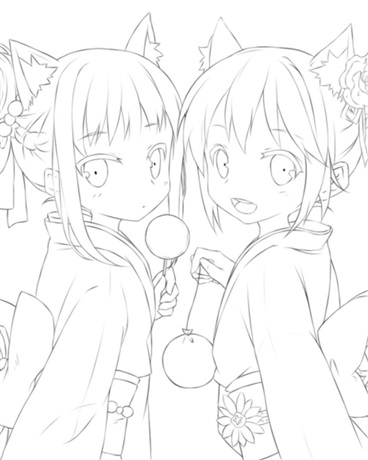花神咖啡屋不可思议的魅魔少女-其一
那时是1933年——就是租界开了快一百年,国权沦丧快一百年,洋场像死之花一样蔓延了快一百年,各种洋人、西洋异族和华人、东洋异族同居了快一百年之时——我进入了洋场的异族租界中一所还算不错的大学学法语:一半是我自己的努力,一半是作为所谓“社会名流的爱才之心”的真人例物——父亲也算是大实业家了,和教育界的几位先辈交流了一下,我就连考试和预科都免了,父亲呢,也捐了些说多不多,但也足以让小市民却步的“赞助费”——一面是为我,一面是换的一个支持教育的美名,用实践证明一下何谓“教育救国”者,来压一下所谓“左翼暴徒”的工人学者的话头。
自然,在大学中我是无聊的,父亲本来也不是为了让我拿上什么文凭搞学术,我没有什么必须好好学的义务。在开学典礼上作为新生代表发言后,我就再也不想回头思考那篇费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写出来的,试图把洪秀全塑造成象征主义异端英雄的夸夸之谈了。自然,“不想回头思考”的,还有我的学业
我之后的学习生活是在舞厅、酒吧和颓废文学中度过的,本来就想让我混文凭的父亲自然不会管。每天和几个狐朋狗友——有西洋的魔法师啦,幻术师啦,搞双修的清教徒啦,唯美派诗人,还有日后很有名的穆时英——每天喝花酒,大声朗读一些不知是激进还是下流的作品,沉溺在妖艳颓废、充满se情的渎神的感官享乐之中。我们伴着穿着透明的改良镂空短旗袍,摆衩开到黑色亮片丝袜的系带的浓妆魅魔夜莺,喝着泡着鲜红、淡紫、圣白罂粟花的烈酒,迷醉在离奇绮丽的幻觉中,在红、绿、粉、紫的光影交织的舞厅里,看着迷亮的萨克斯声里狂颠的舞步,妖柔诱惑的笑声,勾引的倦怠的眼神秋水,樱粉或是猩红的嘴唇......
“你爱我吗?今晚?”
“这话你对多少人说过,小猫咪?”
“可是人们似乎就喜欢这样。堕落啦,颓废啦,享乐啦,感官啦,不都可以在我这里找到吗?不是吗?这不也是一种**么?似乎比起圣洁,妖艳的花朵金钱价值更高,不是吗?所以说......把、我、当、作、人、偶、吧!”
后面是狡黠有意味深长的耳语与暗示性的目光。
大楼的霓虹灯之光如梦幻般弥散在夜色里,玷污了流云与月。
四处都是蓝色、紫色、钢铁、巴别塔一般的高楼、汽车、欲望与混乱。这东方的巴比伦啊,四处建满了物神之殿,四处都是渎神之地。左翼人士也罢(为了好玩,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无政府主义者也罢(我的酒友中就有几个不出名的巴枯宁的翻译者,在舞厅里玩着舞女大腿上的绑成蝴蝶结的蕾丝花带,大呼:“毁灭即创造”),右翼作家也罢,稳健派也罢,新兴神学也罢(他们的修女都只穿透明黑纱修女服),在所谓的议院上、报纸上吵成作团,转头却在酒吧里就达成了和解:喝酒要紧,追女人要紧,为此不惜暗杀,贿赂,抢劫——反正在烟尘之下,钢铁工厂之中,昏黄的月光照不见,上帝的天国照不见,佛陀的慈悲之眼——抱歉,其中有些无神论者本来也不会被看见——西方净琉璃世界照不见。人死了,深夜,装上车,推到江中作罢。层层叠叠的,都市消化不了的惨白的尸体:工人,乞丐,孩子,妖艳浓妆的女体......
那时已是秋天,残花将死,秋雨暗淡,未落叶的树也一片苦绿,所幸被雨洗出一点生气。
下午,我走在街上,很奇怪,昨夜的酒竟然还没有醒,头痛,眩晕,时不时被幻觉和幻听打搅。脚步踉跄。
我似乎精神失常了,长期的纵欲、酒精和迷醉的必然后遗症。
背诵着兰波的《醉舟》,背颂到“在你酣睡漂流的无底深夜,飞起千万只金鸟”,我跌倒了
现在倒在街上,想必一定会死的,一定会死的!可往前走,眼前却是一片模糊,万物都像从飞驰的电车的窗上所看到的那样,跑过去,时代飞速向前,可我们的腿却始终都迈不开,滞留原地,根本看不到一丝可以注意的希望,根本看不到一点可以倾心的信仰。即使生活,又有什么价值呢?像一条狗一样,一面自己被异化、被物化,一面又去异化,去物化自己身边的人——圣洁的修女成了夜莺,比丘尼画上浓妆,纯洁的索尼娅啊......颓废的时代,大概唯一的英雄般的下场就是马尔美拉陀夫一般的死亡吧。
秋雨寒冷彻骨,我躺在凄凉的街上,蜷缩起来,仿佛无助的什么小动物。末日,这就是我的末日了吧。一面哭着,一面把自己抱紧,想象自己在十四或十五小时后就会像众人一样被用袋子装起来扔到江里;像众人一样掉在地狱里,被刺穿。被杀戮、被活剥生吞。
临死之时是这么可怕。
“踏踏”,轻盈的脚步声从漫漫雨幕中飘来。猎艳长久,我凭声音就知道那是女式方口皮鞋特有的声音,有清纯系的狐妖穿过。雨仿佛小了,素素的丁香和栀子香气飘来,少女特有的体香。
“阿拉,先生您看起来喝了很多啊,没事吧?”清脆柔和的声音响起,我抬头,模糊的眼中映出黑色长发的白裙少女的倩影,和头顶一柄青花瓷色的油纸伞。
一切美如希望。
“是死的天使吗?”我在朦胧中小声说。少女抖了一下,然后是银铃般的轻笑。
“不是呦,是莉莉娅呦,莉、莉、娅、呦!对了对了,要去我的咖啡物坐一下吗?”
“冷.......好冷......”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躺在水洼之中,冰冷的雨水几乎要腐蚀入骨。
“客人先生在发烧哦,身上很烫啊。”少女拉起了我的手,“能站起来吗?”
迷迷糊糊之中,一股暖流从少女的手上汇入了我的身体,意识稍微清明了一些。踉跄的,我挣扎的站了起来。
十五分钟后,三个街角之后,花神咖啡屋,立式玻璃旁边,自称莉莉娅的少女店长坐在我对面,眯着眼睛,双手托腮,嘴角扬起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微笑的弧度,显得天真烂漫。
“莉莉娅、小姐,吧?”我换上了冶游时惯用的轻佻语气,喝了一口温暖的意式浓缩咖啡,然后强作微笑,咽了下去。格外难喝。我很好奇,为什么咖啡可以做出来红茶的颜色和味道。
“是呦,十六岁的‘莉莉娅小姐’呦!那,您是什么‘先生’?”
我忽然哑言了。似乎对话展开不太对,我感觉自己被嘲讽着,但又不知怎么接上话头。
“我,余雪雁,OO大学法语系。”我讪讪的回答。
“可你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啊,‘余先生’?”少女微笑着说。
事实上是,我也只是十七岁,本该只是国中生。
“那你看起来也是冶游郎吧,‘十七岁的余先生’?”少女的眼睛睁开了,淡紫色眼眸中流露出了一丝严肃,:“不是吗?这可不好啊。”
“那你是......”什么吗,为什么管我?
“花神咖啡屋的主人。”
“种族......”
“十六岁少女!”这真的算答案吗?或许“少女”是某种隐喻?
“不是魅魔吗?”习惯性的,轻佻的问了一句。问一个少女这样的问题可真是无可救药啊。
“是魅魔呦。”少女认真的说,微笑依旧,“不但是魅魔,还是皇族呦。荣幸吧?”
魅魔,最妖娆的异族,有着令人难以言喻的特性,即爱又恨。
脑子“翁”的一声,然后是令人不愉快的沉默。
“那这么回答你是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少女打破了沉默,歪着脑袋说,“其实都不是吧,‘十七岁的冶游郎余先生’?装出轻佻的样子,跟着别人干荒唐事,现在你一定在想‘这只魅魔的清纯也是一种营销手段’,然后打算习惯性的和我,一只雏魅魔调情,然后.....”少女狡猾的笑了笑,:“骗上床,是吧?”
我忽然哑口无言,一瞬间我似乎被这只黑发少女魅魔的淡紫色瞳孔看穿了我卑鄙猥琐的小丑假面。
“不用担心,物理意义上,还是少女哦。”小魅魔接着说:“但是,不论你怎么逃吧,怎么幻想吧,有一件事是莉莉娅亲眼看见的。”
少女顿了顿:“十五分钟前,在那个小水潭里——在这里还能看见——你躺在那里,在哭哦。”
是啊,十五分钟前,我在哭,孤独,冷,恐惧,悲伤。
“我......”
“你,也是不快乐的存在物啊,‘十七岁的冶游郎余先生’。”莉莉娅抬头看着我,眼中是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色彩,夹杂着同情、悲悯,就算那可能只是魅魔的魅惑术的一种,我仍愿相信那是她此时真实的感情。
“来这里吧,花神咖啡屋!”忽然站起,圣洁的白色裙摆优雅的飘扬,魅魔少女的微笑犹如阳光下的无垠薰衣草花田。
那一天,那个小巷,我就这样和名为莉莉娅的奇特少女魅魔相遇了。
绮丽怪谈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的荒神大人
- 嘛,不太一样的玄穿……至于怎么不一样……呃,自己看看呗!看惯装逼打脸的可以来这瞅瞅
- 3.7万字5年前
- 狼王育成日常
- 为了给读者更加了解角色,加的。(不是因为不想更新)原作——幼女狼王
- 0.1万字5年前
- 异陆物语
- 天出盘云阵,九星连可击。幻灵行千技,不肖人之心。
- 3.9万字5年前
- 想过宅生活的我被迫雇了个大小姐
- 勾搭上绝美千金大小姐该怎么办,当然是好好敲她一笔咯,等等你没钱,不对你要干什么?本店是正规店,你不要过来啊~
- 35.3万字5年前
- 圣愿之战
- “生于万物巅峰之人,存于万物尽头之神,以吾之圣意向你祈祷,吾将以汝之神力,凌于万物之上,以汝之圣愿为吾之神意吾必竭之全力,实现汝之圣愿,汝若以汝之圣愿回应吾之神意,吾将以吾之左臂为介,结下‘圣印’之契约!”
- 5.3万字5年前
- 重生后拥有了忍三的全部能力
- 随便写写看
- 新书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