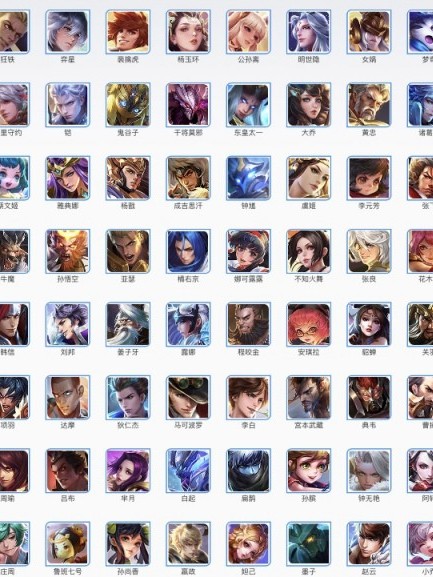二
我跟阿良说。
阿良,我走了。
我看着阿良满是血丝的眼睛。
渴就喝碗水,别忍着,没水要命。
我不知道阿良会不会听我的话,可是我必须嘱咐她。
希望吧,阿良还是当年那个阿良。
很听我话的那个女孩。
我看着阿良憔悴了不少的面容,只好坚强的转身,将双眼背对着阿良。
我走了!
我自以为铿锵有力的说出这三个字,然后朝着门外迈出第一步。
鞋底撞到地上的时候,地上全是土。
我不知道阿良会不会一直看着我出门,但是我知道她的眼睛里肯定有我的一席之地。
等我回来,阿良。
我就这么蔫蔫的说着,也不管阿良听没听到。
反正我是说了。
我感受着迎面扑来的炙热空气,顶着令人窒息的阳光。
村子里的路上没有一点点的阴凉,王老爷子赤着上身,枯坐在他家的土坯门槛上。
他看到我迎面走来。
劳子,干啥去啊?
王老爷子的声音沙哑到就好像喉咙里布满的沙子,声音零碎的磨人耳朵。
去地主爷家借点米.....
我支支吾吾的。
好啊....好啊....能借一斗是一斗啊....反正我这辈子是还不上地主爷家的米了....
王老爷子眼神空洞的好像枯了水的湖,随随便便就能看到底。
那个...王爷,你孙子呢?
平时王老爷子整天抱着的小子此时没了踪影,昨天我就没看到。
好像....我昨天也没看到王老爷子。
送走了。
啊?
卖了。
.....
王老爷子就好像个没有感情的皮影一样,声音平静的让人害怕。
送走了那个兔崽子,不能让他饿死不是吗....
王老爷子说着,搭在膝盖上的手指神经质般的抽搐着。
不能让他饿死在这个鬼地方啊...只能将他送走啊....
再怎么着.....也比饿死强啊.....
那个兔崽子怎么看怎么福大命大.....
菩萨说的....菩萨说的他福大命大......那晚上菩萨托梦给我的.....
王老爷子的声音越来越小,就像口越捞越干的井。
最后井干涸了,王老爷子也不说话了。
我只好站在王老爷子的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连告别的几个字都卡在喉咙里钻不出来。
这时,王老爷子身后的门打开了。
王老爷子的儿子从门后探出头来。
他的嘴唇上一道道的全是小小的疤痕。
爹,您来看看。
嗯....
王老爷子支吾一声,颤颤巍巍的扶着墙头站起身。
王老爷子的儿子礼貌的朝着我低了一下头。
而我的目光却越过他,顺着门的空隙看到了王家院里。
两口棺材,还有王家的儿媳妇一脸死灰的靠着棺材。
直到王老爷子轻轻的关上他家那扇有些腐朽的木门。
我只好继续朝着地主爷家的方向走去。
劳哥?
身后的小小的声音使我猛的转过头去。
张耙子就站在我身后。
劳哥你也要去地主家借米吗?
张耙子小声的问道。
嗯。
我也去,咱俩正好同路。
张耙子有点找到伴一样的喜悦,他露出了几乎都看不见的笑容。
那个....
我还想着要怎么跟他说。
节哀啊.....
啊.....
张耙子闻声一愣。
啊,没事啊老哥......
他好像很无所谓的说道。
儿子还会有的....我现在得养活我爹娘和我媳妇。
他僵硬的翘起嘴角,声音却带着一丝颤抖和沉重。
你知道吗?我王老爷子刚才把他家的孙子给送走了.....
张耙子岔开了这个令人无比尴尬的话题。
我知道。
我说。
唉....其实我也有把我家那个娃子给送走了的想法...只是我媳妇和我爹娘都不乐意啊....
那时候我爹还操起烧火棍狠狠的给了我几棒子。
我不知道我爹娘和我媳妇现在是怎么想的...我是真的后悔啊,当初没有把我家的娃子给送走。
起码我....我....不会亲眼看着他死啊.....
张耙子越说,声音越曲折。
行了行了....
我连忙打断了他的话。
然后我也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俩就走在荒凉的村子里。
白婆婆家茶馆的旗子被扯的七零八落的,她幸好有一个在外地做生意的儿子,听到老家大旱,连忙把自家的老娘给接走了。
铁匠师傅的铁匠铺倒还是开着门,只不过铁匠师傅趴在桌子上整日整日的不停打瞌睡,火炉也没升起来。
张耙子瞟了一眼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的铁匠师傅,而我则看也没看一眼的就掠过了他的铁匠铺。
我们继续沉默着,直到到了地主爷家的大院前。
王管事刚刚骑上一头有些瘦的驴子,他坐稳之后就看到了我俩。
劳山?你来了?
王管事有些惊讶的看着我。
啊...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朝着王管事说道。
我.....
我和劳哥来找地主爷借点米。
张耙子直接就朝着王管事说道。
王管事一愣,他打量打量张耙子,又深深的看了我几眼。
......
他轻轻的舒了一口气。
来吧,他说。
我带你们去见老爷。
地主爷家院子里的那棵柳树也枯死了,还有一大片的花圃。
现在都只剩下凝结的土坷垃和漂浮在地表上的柳树树根。
昔日算得上是五颜六色的大院子,如今也干的只剩下土味和灼热的呼吸。
我的呼吸有些沉重,脚步也有些局促。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来地主爷家里借米了,总之就是不好意思再来了。
我没有张耙子那样的勇气去和王管事那么直接的说出自己的愿望。
自己还是....又不比他张耙子差点什么....
我正胡思乱想着,突然就觉得自己左边有什么东西一样。
我下意识的挡住了左边撞过来的东西。
我感受到了一点点的温暖,还有香味。
好像地主爷家里的花圃还没有枯萎之前,那种全村里都有的淡淡的花香。
我看向自己挡住的东西。
小姐!您怎么出来了....
王管事急急忙忙的拨开我的手,将女孩小心翼翼的扶了起来。
他轻轻的搀着女孩的双臂,将女孩扶到台阶上坐下来。
小姐,您的伤还没好,怎么就跑出来了,您怎么就不从屋里好好休息呢.....
王管事七嘴八舌的说道,他显得特别的紧张和不安。
女孩闷闷的听着王管事不停的责备,嘟着嘴,好像很后悔一样的表情。
来人!来人!把小姐扶回去!
王管事大吼两嗓子,一个侍女模样的女孩急急忙忙的跑了出来。
你怎么照顾小姐的!你怎么能让小姐自己跑了出来?万一小姐在出什么事情你这条贱命根本就担不起知道吗!
愣住干什么!快把小姐给扶回去!
侍女被王管事责骂的好像要哭出来一样。
两位.....抱歉,让两位见笑话了....
王管事的话之间顿了一下。
我这就带两位去见老爷....
地主爷坐在正坐上,我和张耙子站在他面前。
米啊....我其实也没剩下多少了....我昨天刚刚让我二儿子去别的地方买米去了.....
地主爷一脸忧愁的说道,他还有些苦涩的叹了口气。
昨天一大早,地主家的二公子继着大公子也带了一只车队朝着城里那边走了。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和地主爷说,张耙子却直接咣当一声跪在地上。
爷!求求您借我十升米吧....您知道我小儿子才饿死不久....
十升啊.....我被张耙子张嘴要价吓了一跳。
张耙子确实还有一个儿子.....可是这十升要的也有点太多了....地主爷也不知道给不给.....
十升......有点多啊....
地主爷说道。
张耙子,我知道你家人不少,可是我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
张耙子好像没有听到地主的叹息一样,头顶着地,响亮的磕了三个响头。
地主一声声清楚的听完这三声响亮的磕头,脸色变的有些难堪。
他先是看了仍然头顶着地的张耙子一眼,然后深深的又看了我一眼。
还没等他开口,我直接就张口说道。
老爷....您找我有啥事情,我都答应了....只要您借我俩米就行.....
地主爷的眼睛里先是闪过了一丝丝的光芒,还有....
地主爷身后的屏风之后,也许是风吹的稍稍颤动了一下。
还有手指骨骼间清脆的一声响。
你....说到做到?劳山,你说道做到?
嗯,我说道...做到。
我顿了一下。之后挺直了后背,说道。
好...好....
地主爷的眼睛里精光大放,他朝着屋外大喊。
王管事!王管事!
声音刚落,王管事一脸严肃的小步走进门。
老爷,您找我。
你去....你去带着张耙子装十升米给他......
地主爷指着张耙子的手指都有些兴奋的颤抖。
然后你再打十升米交给劳山。
地主爷说完,看着我说。
我给你十升米...之前的米你以后也不用还了.....
十天之后,十天之后你过来,十天之后你过来......
别忘了....十天之后你过来。
地主爷边说边走到我面前,他狠狠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张耙子闻声兴奋的又狠狠的朝着地主爷磕了两个头,然后跟着王管事走了。
可是地主爷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一样,他和我说完,就背过身去。
可惜他的手颤抖的根本就停不下来,抖得像个筛子一样。
地主爷面对着他身后的那扇屏风,不知道他....他可能没听见,屏风后的那一点点声音。
应该....是地主爷家里来客人了吧...
我还是别告诉地主爷了。
一旁有个侍女端了一杯茶水放在我面前,然后悄然走出了屋门。
脚步很轻,却牢牢的扎在地上。
咋就又....想道这些东西了。
我有些珍惜的一点点喝完茶水,然后将杯子轻轻的放在桌子上,尽力没有弄出一点点的声音。
这时,王管事重新出现在门口。
你去吧,劳山,你去跟着王管事打十升米。
这时,地主爷转过身来,看着我。
他的眼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
像千斤的巨石朝着我压过来一样。
我朝着地主爷深深的鞠了一躬,尽力无视他沉重的目光,跟着王管事走出门去。
黄昏从天的那头换上了一道锁,沿着我回家的路。
不知道何时,天都已经黑了,没想到借个米的功夫居然就是一天。
.....
心里满满的都是喜悦。
可是总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和焦急混在喜悦之中。
感觉很不好。
尽早回去吧,趁着天还没黑。
我加快了回家的步伐,每一步都溅起地上大块大块的灰土。
可是我越走越快,溅起的灰土也越来越小。
很久了,我都没有走的这么快了。
就像小时候,那些追着买糖人的小孩子们一样,穿着锦缎的棉袄,小腿一深一浅踩在厚厚的积雪里.....
积雪里......
我怎么想到了这里?
这种火热的天,我居然想起了当时的大冬天。
雪下的那么大,阿良和闺女穿着锦缎缝纫的棉袄,围着小火炉,火炉旁摆着一张小桌子,娘和阿良,还有闺女都坐在小桌子上。
小桌子上摆着肉,还有闺女最喜欢的糖丝里脊和阿良最喜欢的从聚德福买来的醋蒜。
醋蒜腌制的晶莹剔透,好像阿良腰间的那块玉玦。
闺女的口水止不住的流,娘夹起一块里脊,故意从她的小孙女面前绕啊绕。
那时窗外下着大雪.....
我好像感受不到肩上十升米的重量。
我....扛着十升米干什么呢?
我给谁扛着的十升米呢?
没了米就去买啊,为什么要....要我去扛?
随便找个小厮,不就好了?
这种事情为什么要我来做?
我满脑袋都是懵懵懂懂的,好像一个刚刚初生的孩子,看着面前陌生的烟火。
也许是本能,我就这么迷茫的走到了家门口。
我推开大门,将米放在院子里。
我推开屋门。
我....呼喊着阿良的名字,还有闺女的名字。
我....到底有没有喊她们的名字?
我怎么什么都听不见...
谁.....谁哭呢?吵不吵啊?
我猛的推开屋门,我看到,阿良跪在地上,她的眼眶红红的。
闺女的脸色在黄昏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无比惨白。
阿良看着我。
她不停的抽泣着。
我....我只好看着她。
看着她慢慢的抓起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到炕上的一把剪刀。
然后狠狠的,朝着自己的心窝刺去。
我....我居然什么都没做。
我他妈的....他妈的居然就那么看着.....
我看着滚烫的鲜血溅了我一脸。
阿良好像仇恨愤怒的看着我,缓缓倒下。
所以说....到底刚才谁在哭?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干涩的不行。
还有沙沙哑哑的,撕心裂肺的哭声。
是我在哭......我在哭....
我在哭.....
我猛的惊醒。
耳边撕心裂肺的哭声还在响着。
张耙子家的大儿子也死了吧,我清楚的听到了张耙子和他媳妇的哭声。
还有两个苍老而悲戚的哭声。
我靠着墙坐起身。
看着窗外。
还是那么的干涸,裂开的大地还有天边。
不是黄昏罢了,而是晨曦。
连公鸡都无力啼鸣了,在这撕裂天边的哭声和晨曦光芒里。
晨曦的光芒都透露着灼热的气息。
天啊,又要黑了。
我的目光不小心触碰到自家的小小院子里,还有炕上的两个被子。
我盖一个,我娘盖一个。
娘的被子我还留着,被我叠的很工整。
只是我自己盖的被子从来就没有叠过。
院里也一样,除了那颗早就被我砍了的杉树。
一切都没变。
我看着窗外,听着张耙子家的哭声。
有点想哭。
**妈的,有点想哭。
明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正在玩游戏的我穿越了
- 本应还在玩「洛浮因」这个游戏的少年不知为何带着这个游戏的系统来到了这个时代主角:“狗作者!老子怎么变成了声柔易推倒的那种萝莉!”作者:“你是主角,你身上压着武林的所有希望!俗话说得好胸不平何以平天下!”主角:“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 9.9万字5年前
- 飞升失败的我沦为武侠世界大反派
- 我才不要当反派
- 22.5万字5年前
- 拯救我的魔堕师尊
- 许多年以后。苏白屹立苍穹之上,望下四方诸侯。淡漠念着。“就这就这就这就这就这??”————————————月票给老书!砰砰砰!
- 26.0万字5年前
- 进大牢吧崽种
- 哈?父亲升仙了?哈?他以前是开茶楼的?哈?现在我要接管茶楼?……茶楼里怎么还卖酒啊??……本书中的一切名人皆为虚构,请勿拿历史上的人物来比对,封面来自于网络,不定时更新
- 4.7万字5年前
- 落跑天尊依旧被众仙子追逐中
- 【群号:274466614】“开房!要最好最高端的的牢房!刑期越长越不嫌长!”——浩气仙盟十大杰出青年、海陵仙宗道德小标兵、玄戈峰二当家、四海游侠、南无驮么舍身菩萨、否天、侠义的化身、正义的伙伴、义气千秋小郎君:晋玉。“我就是想被抓起来,为什么这些仙子的眼神这么可..
- 21.7万字5年前
- 属太阳的腹黑王者荣耀英雄
- 简介:21世纪的一个穿越腹黑女,特别喜欢是毒药什么的……但是偏偏这样的,腹黑属性,却是属太阳的,走到哪哪里都是一堆迷妹和喜欢的小哥哥……
- 2.3万字5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