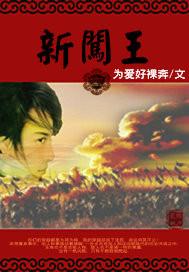第616章痛打张翼
翌日,二十艘蚊子船驶向大沽口,去和白朗宁的常胜师汇合,这两支军队由李国楼指挥,先安扎在大沽口军事基地。李国楼率领一百多名戈什哈离开海港,直奔天津卫,李国楼去找开平矿务局的督办张翼算账,战争机器已经开动,想要赢得胜利,先要消除自身的隐患。张翼位高权重,只有他亲自出马,才能解决北洋水师的后患。
他才不会讲道理,枪杆子在手,谁敢不听他的话,就使用暴力。李鸿章出巡也没李国楼带的兵多,两宫皇太后特许李国楼随行护卫可用一个营的兵力,李国楼还算有节制,护卫队没有满编。吃一亏长一智,李国楼不再随性枉为,故意表现得嚣张跋扈。
一路上马队踢翻菜农的篮子不计其数,督导队军官随势扔出几枚铜钱,喝道:“快点闪开,不要命啦!”
菜农欲哭无泪,捡起地上的铜钱,叫道:“多谢军爷的赏钱。”
护驾的车队两边的戈什哈,趾高气昂的甩动马鞭,不让百姓靠近车队。前面开道的戈什哈人马精神,大嗓门不断叫嚷,“闪开!”
“让道!”
黄小曼从车厢里看到外面大街的场景,沿途的商贩被李国楼车队搞得鸡飞狗跳,一点也没有高官过境的威仪。
“小楼,你可以鸣金开道嘛,这才像个大官。”黄小曼拉好窗帘,不去看车窗外的景色。
李国楼伸出两根手指,说道:“安全第一,速度第一。十夫人,想杀我的人太多,不能让任何可疑之人靠近我,我的儿郎为了保护我的安全,虽然做事极端了点,但这是必须的。”
李国楼言尽于此,没有说下去,就算手下的戈什哈撞死路人,他也会包庇手下人。敌人就隐藏在百姓之中,窥探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一遭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李国楼被黑龙会袭杀过,如今出巡小心翼翼,就怕敌人对他发动偷袭。
“哎!小楼,你千万不要有事,我可不想改嫁。”黄小曼无奈的搂住李国楼,把头靠在李国楼肩上,是她自己选择这个男人。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悦,肥马轻裘,过着富足的生活。同样担惊受怕,害怕灾难会降临这个大家庭。
李国楼暗自腹诽,家里的夫人没几个贤良淑德,不给他戴绿帽子,就算祖坟冒青烟了。
李国楼抚摸着黄小曼那满头的青丝,恋恋不舍的说:“放心吧十夫人,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也要提高警惕,出门一定带着侍卫,他们是最忠诚的卫士。若是犯了小错,就要狠狠的惩罚。但若是人命关天,就要袒护他们。”
“小楼,你怎么都是歪理啊。”黄小曼挣脱李国楼的怀抱,怒瞪李国楼。
“嘘嘘嘘!”李国楼低声:“我的小宝贝,这就是一个比喻。我当然希望每个手下人都克己奉公,但那群王八羔子得意惯了,总有冲动的时候,就像我当初杀人一样,上面有人罩着我,才有我今天的成就,我当然也会罩着手下人。”
“哦!我懂了,眼不见为净。”黄小曼闭上眼睛,不再去想那些被戈什哈欺凌的菜农。
新武军进入天津城,看城门的蓝翎长毕恭毕敬的敬礼,进入城内车队放缓了速度,迈着整齐的步伐,直奔张翼的府邸。早有探马侦知张翼正在家里大摆寿宴,唱大戏贺寿,张府里高朋满座,天津卫有头有脸的官员都在张翼的家里。
李国楼稍微踌躇一番,便定下决心,要给天津的官员一个下马威,喝道:“魏群、阿里郎,给我把张翼家的门,前后堵上。把张翼抓起来,本官谁的面子都不给。谁敢反抗,就给我打,若是有护院的人敢拔刀,就给我开枪警告,若是对方敢开枪,就给我打成马蜂窝。”
“是!”魏群、阿里郎抱拳疾行,天塌下来,由李国楼顶着,他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军令为天职,就算前面是龙潭虎穴也敢闯。
虽然已过正月十五,但张翼还没从春假里舒缓过来,早上点卯之后,就从天津开平矿务局溜回家里。
张府披红挂彩,鸣锣开戏,宾客临门。已过午时,酒席已经撤下,八桌宾客坐在大堂里听戏,张翼陪同知府张名堂,坐在宾客中间,享受众人的吹捧。
张翼原为醇亲王奕譞府里的外府管家,是醇亲王的家生奴才,因能说会道,又识文断字,被醇亲王认为是可用之才,放出王府,出来为官。迈入仕途十几载,已步入位高权重的岗位。
开滦煤矿出产优质煤炭,而且是富矿,为大清国有煤矿,当然开平矿务局的最高长官的位子,富得流油,一年捞十几万银两不在话下。想捞更多的话,就要看长官的心,够不够黑。用张翼话讲,“全靠醇亲王恩典。”
此时张翼坐上开平矿务局的督办之职还没到一年,事业如日中天,自认国家栋梁之才。
“伊人月下戴红妆,不知伊人为谁伤,鸟儿尚成双,相依对唱忙,怎奈伊人泪两行。
伊人独唱伴月光,唯有孤影共徜徉,柳叶裙下躺,貌似心亦伤,与伊共叹晚风凉。
人说两情若在永相望,奈何与君共聚梦一场,戏中人断肠,梦中暗思量,自问手中鸳鸯为谁纺······”
舞台上歌姬婉约优柔造作的唱戏,舞台下一群衣冠禽兽击节叫好,正在拍手鼓噪。张翼色眯眯的看着婉约柔弱的腰肢,哈哈大笑,天津的头牌歌姬婉约来给他贺寿,这是张名堂给他面子,谁都知道婉约是知府张名堂包养的歌姬。
张翼猜度着张名堂看中他的哪个歌姬?两人互换有无,玩一个月,享受不同的乐趣。张翼贼兮兮问道:“府台大人,你看中哪位?”
“这个嘛······”张名堂扫视一桌莺莺燕燕,张翼家里果然金窝藏娇,一个个都是那么可人,让人垂涎欲滴。
师爷张掖心领神会,凑在张翼耳边,低声道:“督办大人,一换二,二个月为期如何?”
“啪!”
张翼和张名堂击掌为誓,这种勾当已成官场潜规则,同道中人乐此不疲,歌姬是玩物,理应在市场上流通。这种习俗已成社会风气,上行下效,长官玩高档的歌姬,下面的官员玩低等的货色,笑贫不笑娼的社会中包养成风。
张府里面正在鸣锣开戏,府门外已经开打了。上百名新武军战士手持刀枪,将宾客的车夫、侍卫打翻在地,把张府包围起来。有几个官员的侍卫还想反抗,拔出左轮手枪。
“啪!”
魏群率先开枪,喝道:“臭小子,看清楚我们是新武军,谁敢动一下,打成马蜂窝。把枪给我卸了!”
官员的侍卫哪敢真的开枪,这么多长枪顶在脑门上,乖乖的缴械投降,嘴里不依不饶道:“新武军的军爷,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来天津卫乱来。没钱也不能炸营啊!”
魏群大声吼道:“王八羔子,都他妈的给老子闭嘴,一切与你们无关,我们是来抓张翼。”
“哦······”大门外的一群马车夫、轿夫,全都放心了,不乱动就不会吃枪子。
新武军战士对官员的侍卫还算客气,缴械之后,没对这些人施暴。对张翼府里的仆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谁敢反抗就是皮鞭、枪托伺候。
那个府里的总管言语威胁了几句,便给新武军战士打得昏死过去,肋骨断了算是小伤。
金银来吐一口唾沫,喝道:“少他妈的装死,老子叫五积子,天底下没怕的人,老东西回头再来找你算账。”说完金银来一挥手,带领一群战士冲入张府。金银来心中窃喜,今天这场架一打,明天说书人的桥段里,就有他“五积子”的名号了。
张府里面哭声一片,以为张翼招来滔天大祸,要被抄家灭族了。张翼和张名堂听见外面嘈杂,还没明白所以然,大堂已被荷枪实弹的新武军战士包围了。平时作威作福的一群官员,面对着上堂的枪,个个吓得脸色惨白,以为新武军造反了。
还是师爷张掖最会看脸色,认出是新武军的装束,好像见过这群军人,眯眼仔细辨认一番,看见李国楼的走狗金银来,两人还一起喝过酒。李国楼可是敢动用金牌令箭乱来之人,一看今日的阵仗,便知李国楼又跳起来了,给李国楼背后撑腰之人,那是连同治皇帝也不敢得罪之人,他是没胆量去和李国楼较量。
张掖急忙挤出笑容道:“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金队长亲自出马。天津知府大人在此,你可要给个面子。”
金银来手里的左轮手枪顶了一下大盖帽,痞子腔:“张师爷,这里没你什么事,别把自己弄脏了,都察院右都御史马上就来,都给我站好了。”说完金银来阴毒的一脚踢在歌姬婉约脚的内关节,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直接让婉约摔倒在地上。
婉约吓得嘤嘤直哭,不知哪里得罪了军爷?金银来阴笑道:“臭表子,再敢哭一声,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小银刀亮晃晃,闪着银光,婉约吓得索索发抖,捂住樱桃小嘴,眼泪婆娑流下,就是不敢发声。
张名堂看着自己心爱的歌姬婉约被人欺凌,怒火万丈,大喝一声:“大胆!”
张掖随势一脚,暗踩在张名堂官靴上,暗示张名堂明哲保身,静观其变,不易在此时和李国楼翻脸。
张名堂久经官场,立刻领悟张掖的深意,急忙表现出儿女情长,冲上去保护婉约,好言安抚婉约,趁势扶着婉约离开大堂,这种场合不易表态。张名堂抛弃酒肉朋友张翼,把适才击掌为誓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临走,张掖抱拳道:“山水有相逢,金队长改日咱们再约。”
这有些威胁的语气,金银来一把拽住张掖的辫子,活生生把张掖提溜回来,狞笑道:“张师爷,有什么话尽管说,长官都在,不用再约。”
那头发被人硬扯的滋味,张掖平生第一次感受,疼得他泪水横流,终于领教金银来的厉害,果真如江湖所说,金银来是李国楼杀人的一把刀。急忙讨饶道:“金队长,赶明我请客,就是这意思啊。”
“嗯······没事的人,请吧。”金银来让出一条道,戏孽的看着众位官员,想看一看有多少官员,敢跟李国楼作对。
张掖打定主意要傍上李国楼这颗大树,回去就劝知府张名堂,要跟李国楼一个鼻孔出气,无论发生什么事,坚定的站在李国楼一边,李国楼是大清复兴的功臣,与李国楼交好,百利无一害。张翼的破事,连边都不要沾,虽然他还不知张翼为何得罪李国楼?但得罪李国楼的下场很恐怖,这一点张掖深信不疑。
须臾之间,大堂里的官员走得差不多了,只有谭家戏班子还留在原地,他们是张翼请来唱戏的,赏钱还没拿呢,现在一走,不可能再来讨赏钱,那是要被张府的人打出去。班主谭月楼认识李国楼,叫手下的戏子别慌,呆在原地,万事有他开口。
“右都御史到!”马德全高声道。
张翼被绑成粽子一样,跪在地上,看见李国楼,叫道:“张翼无罪,李国楼,你凭什么抓我?”
“就凭这个。”李国楼捏住张翼的鼻子,倏地把一块煤炭塞入张翼的大嘴,怒骂道:“驴球子,竟敢欺骗北洋水师,想发财想疯了,连傅相大人也敢骗,给我先打五十鞭。”
马德全抽出鞭子,还没动手,金银来抢步上前,叫道:“让我来!”
张翼有冤无处申,痛彻心扉,婆娑娑流泪,昏死过去。
晚清神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秦惠文王
- 简介:让我们回顾一下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孝公的下一代秦国君主,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君主,使变法发扬光大的君主秦惠文王的一切!
- 4.4万字6年前
- 战地枭龙
- 简介:武警排爆能手张天骁,在排除二战日军遗留武器时,穿越到抗日战场,在地下党员老曹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时值“皖南事变”爆发,为了掩护战友突围,张天骁临危受命,斗军统、惩汉奸、杀小鬼子,拉起一支纵横大江南北的抗日队伍……本书数字版权由“当当”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115.0万字6年前
- 新闯王
- 简介:你们的穿越都是为将为相,我的穿越却成了流民,命运何其不公?本想置身事外,但人和事推动着猪脚,一步步无奈加入到这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之中.主角也不是全能人物,敌人也不是猪一样的愚蠢.没有一帆风顺,只有不断跌倒爬起.这是一个斗智斗勇,忠诚与背叛纠结的热血传奇故事,给大家一个全新思路和全新感觉的明末天下。“我的中国梦”主题征文本书数字版权由“中文在线”提供并授权话本联合销售,若书中含有不良信息,请书友告之客服。
- 263.2万字5年前
- 卡蒂
- 简介:新大陆,新征程
- 3.2万字5年前
- 听史诉说——吴溪桐著
- 暂无介绍哦~
- 25.8万字5年前
- 战斗在红色帝国
- 书在多年前已经有了,业余写写,写的不好,欢迎大家斧正。发在某点,某横,某血都被和谐了,十年了,争取下个十年内完结。
- 8.1万字5年前